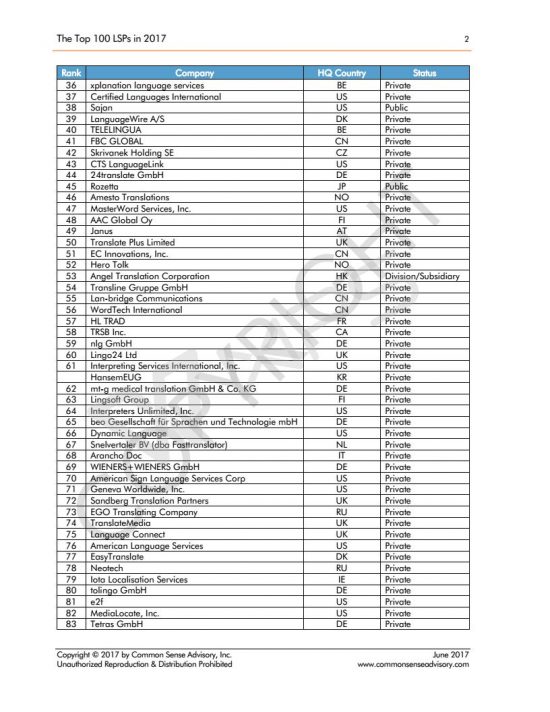本版撰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雯洁
日前,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自媒体频道今日发出消息,将众筹重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开出了“史上最高翻译费”:500元/千字。对此,有人质疑,用这种众筹的方式来翻译和出版经典的做法是否有些草率、不够严谨,是否能够保证翻译的质量。其实,经典著作的翻译对于译者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即使是重译也在所不惜,《莎士比亚全集》、《堂·吉诃德》、《老人与海》……许多经典名著的中译本层出不穷。如何看待这种经典重译现象?
名著中译
莎士比亚全集
1921年和1924年,田汉分别用白话翻译了《哈孟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成为第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中国人。
1930年,尚为青年的梁实秋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直到1967年他年过花甲才译完在台湾出版。梁版《莎士比亚全集》包括戏剧37卷、诗歌3卷。被公认为译得比较直白。
1936年,朱生豪开始翻译莎剧。1944年底他因病早逝,留下31部半译稿。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朱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共计27部剧。此译本一出,好评如潮。
1957年,台北世界书局以此前27部朱译为基础,加上虞尔昌补译十部历史剧及莎士比亚评论,出版了37部剧作的《莎士比亚全集》。这是华语世界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
从1960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启动了组织国内专家重新校订补译莎剧全集。1978年,《莎士比亚全集》六卷本出版,张谷若、杨周翰、章益、方平、吴兴华等专家参与其中。这是内地迄今为止公认的权威版本。
2014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已故莎学家、著名翻译家方平先生主编,由方平等8位翻译家采用全诗体翻译的10卷本《莎士比亚全集》,收入了莎士比亚迄今所有被学界认定的39个剧本及其他作品,被认为是整个华语世界最新、最全的诗体译本。
堂·吉诃德
1922年,《堂·吉诃德》的中译本最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两卷本《魔侠传》,用的是文言的形式,只翻译了上卷。
1959年,又出版了傅东华全译本,而后,还出版过刘云、伍实、常枫等人多种不同形式和不同书名的译本。但这些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直到1978年杨绛先生首次从西班牙语原文(1952年罗德里格斯·马林校勘本)翻译了《堂·吉诃德》,首版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1987年推出修订版。
1995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西语学家董燕生教授翻译的二部全译本《堂·吉诃德》,2006年改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插图特装修订本。
200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部全译本《堂·吉诃德》,由西语学家孙家孟翻译。原版书中塞万提斯自己写了11首赞美《堂·吉诃德》的诗,孙家孟将11首诗全部译出置于正文之前。
老人与海
1954年,张爱玲翻译了《老人与海》,成为中译者第一人。2012年,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张爱玲译作选二》出版,其中收录了《老人与海》的张爱玲译本。
自1979年起,《老人与海》的中译本大量出现,如: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初版,译者李锡胤;漓江出版社1987年初版,译者董衡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初版,译者吴劳。翻译家吴劳的版本被公认为是十分出色的译本,文中还有许多附注。
201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新版《老人与海》,采用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的译本。据其译序所说,译文早于1952年开始连载,应是此书最早的中译,1957年由重光文艺出了繁体字版。
正方
有人觉得重译有意义就不必禁止
羊城晚报:不久前,吴晓波书友会众筹重译《国富论》。一百多年来,《国富论》经过多次重译,至少有七八个版本。有人质疑,经典是否需要重新翻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赵武平:就拿这个事来说,他们并不是全篇重译,我觉得更像是自娱自乐的事情。有人有时间、有精力,并且觉得做这个事情有意义,就可以去尝试;如果能吸引更多的人对名著感兴趣,当然是好的。在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时代,没有理由禁止别人来做这个事情。
而从专业出版的角度看,理论上讲,一本图书只要是没有版权,也就是说,它的作者去世50年以后,版权就进入公共领域了,谁都可以翻译。只要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就没有能不能重译这个问题。至于翻译出版后能不能得到学术界承认和读者欢迎,甚至达不达得到出版社的出版要求,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豆瓣、译言也在不断翻译各种各样的书,其实没有关系的,就跟写小说一样,你写得好,译得好,你点击率高了就算是得到承认了。
羊城晚报:有专家说经典著作在过去已经被翻译成许多版本,而其作为畅销书,市场已经较为饱和,没有更大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源于当前的翻译水准,也很难有更值得期待的翻译,认为译旧还不如译新。您认为呢?
赵武平:其实名著重译的工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从专业出版来看这个现象,一本名著能够出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可以说一定是一个人类知识集大成的智慧传承的典范作品。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故事,无论是法文的、英文的、德文的,还是俄文的,它进入中国总是要找一个最合适讲故事的人,大家才愿意听,或者说听故事的人才能更大限度地还原和感知故事本身。那么,一个名著的译者很可能是在相关领域里有一定专业研究和学术地位的人,他翻译出来的译本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这个又并不是绝对的。
翻译和写作在不侵犯知识产权和版权的情况下,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行为。因为读者也有层级之分,普通的、成熟的、专业的甚至学术的,他们在不断地成长,也在不断地筛选、比较,讨论译本的好坏,是否超过原有译本的学术水准等,这都不是太难的事。就跟一支贝多芬钢琴曲一样,家里有钢琴的都可以弹,但有没有可能进行表演,甚至是售票开音乐会,这个市场及读者都是有鉴赏能力的。我们无须担心译本是否有过多版本,实际上,大部分重译的书是不存在的,或者站不住脚的,因为学术界和普通读者都在不断地做这种淘汰的工作。就像现在大家说网络写作的人很多,挣钱的也很多,但是把成名的和不成名的比例进行对比,就发现在这种学术工作尤其是有难度的著作翻译上,不仅是你站出去吆喝一句五百元千字就能完成的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也就是说,能否靠译书站得住脚,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旁观
粗制滥造的重译没有必要
羊城晚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曾说过,新译应该尽可能不同于旧译并高于旧译,否则,就没有什么重译的必要。但对于经典的翻译,有的读者表示有缺憾,比如期待更符合当时语言、时代气息、读者阅读审美习惯的译本。那么,重新翻译就成了弥补缺憾的一个选择。您对此怎么看?
赵稀方:我们从现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实际出发,基本的情况是,中国进入版权公约后,现在大量地重译经典名著,因为新书需要买版权而大部分经典名著不需要,再者,名著本身是畅销书,是不会过期的。商业利益的驱动导致现在重译作品泛滥。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名家的译本是跟出版社有合约的,出版社可以重印;但有些没有版权的作品,只能采取重译的方法出版,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只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些出版社为了出版而出版,其本身的想法并不是将作品译得更好,而是为其贴上“新译本”的标签。这种现象在如今的翻译出版界普遍存在,造成译本水平极其粗糙。这是我们反对经典重译的一个现实考虑。
羊城晚报:这或许也是一些读者迷恋经典译本拒绝新译本的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许多伟大的译本,通常并不是最老的译本——也就是说,傅雷先生们,也曾经是“新译本译者”。就是说,已有的较好译本,并不成为“以后不需要重译”的理由。否则林纾先生之后,也不用再翻《茶花女》了,李健吾先生的《包法利夫人》之后,周克希也不用翻译了。这个您怎么看?
赵稀方:这就涉及到一个翻译水平的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可以有的,新译本匹敌“旧译本”在我们翻译研究来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杨绛翻译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本身就是个很好的译本,但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教授董燕生发现了杨绛译本的一些错误,由于他精通西班牙文,翻译水平很高,并且精益求精,最后他也译出了一个水平相当的译本。还有一个例子,关于《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无论是梁实秋还是朱生豪的译本,都是散文体,而后来方平主译了诗体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这个就比较好,因为作品本身就是诗体的,这种重译我认为也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像这样译出比名家名译更好的作品,我们当然是欢迎的。但你要知道,超过名译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翻译家倾其一生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么高的水平,更何况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要挑选这样一个译者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到底,如果你的水平能够超过前人,当然欢迎,否则粗制滥造的翻译就没有必要了。
反方
重译耗费时间和成本,意义不大
羊城晚报:对因《国富论》重译出版引发的经典是否有必要重新翻译的讨论,您持何看法?
陈及:只要没有版权问题,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重新翻译出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至少认为,反复地重译是没有必要的。首先,经典是一种常销书,基本上一直都在销售,就以《国富论》而言,过去出过很多版本,并且这些版本在今天仍旧在刊行销售,不存在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任何人想买,都能买到,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其实是已经被满足了的。而且就目前的翻译水平而言,总体上是比不上前人的翻译的。那么,经典重译本身除了时间和成本的耗费,我认为社会意义并不是很大。而且众筹在中国是一种市场行为,恰恰和经典翻译需要的严谨、沉稳等条件相悖,因此,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两边都没有结果,既赚不到钱,也做不出来好书。
羊城晚报:您刚才提到翻译的问题,有些读者正是认为过去常见的译本或多或少存在着,诸如词汇翻译跟不上时代、专业语汇使用不当等问题,所以才期待更符合当时语言、时代气息、读者阅读审美习惯的重译作品,这也是介于“精确”和“通俗”进行重译的理由。
陈及:即便是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很多著名的译本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大家会有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新译本也依然不能保证文本就能让所有人满意。一方面是翻译能力的问题,不论是翻译效果的信达雅,还是翻译者本身的功底、学术态度,等等,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些年代较为久远的经典译作,对其做局部的调整,我认为是可以的,但要所有东西推倒重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或许产生的问题会更多。
羊城晚报:一些读者会迷恋经典译本而拒绝新译本,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家,也曾表示情愿一遍遍重读林纾那些存在“漏译误译”的西洋小说,也不愿读后来出版的尽管也比较“忠实”的译本。“经典译本”是否就是拒绝新译本的理由?
陈及:像钱钟书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看所有译本可能都有问题。但是经典是很庞大的体系,能读经典的人都是小团体、小圈子,一般的读者你给他,他也接受不来,专业能力还没入门。经典的作品中国老的前辈也翻译得差不多了,现在老教授也没时间去重译,多半是一帮学生去弄,七弄八弄的,水平参差不齐。又何必浪费时间去做重译工作?在今天,翻译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时代,但质量的下降也是众所周知,错漏百出、不忍卒读的现象比比皆是,现在找到一本没有太大问题的翻译书籍很难。我们的翻译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不追求质量。不论是译者还是出版者,都有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阅读普遍浮躁的时代,年轻人们更多习惯于屏幕前的阅读,对于经典的兴趣相对较少,谁还去关注那些几百年的经典呢?谁还会专门拿出时间去下工夫读那些大部头呢?
羊城晚报:经典市场饱和,翻译难有新突破,依然不妨碍经典被反复重译。但我们发现,许多新的、世界前沿的著作,却不一定被及时翻译引进。
陈及:经典往往是最朴实的道理、最基本的原理,是开放性的;翻译和出版经典,当然有它的作用。相对来说,今天新的著作和研究,会显得零散而具体,我们的先人早已经把大道理都说完了,后来的人,很少有开创性的,大多都是在经典的基础上不断地重新论证、重新表达,或者在局部的问题上更加深入。尽管新作很少有经典那种奠基式的作品,但依旧应该多翻译,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离得更近,更具有指导意义。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经典中的基本理论,其实早已经融入到了现代理论之中,如《国富论》这样的书籍,它论述的是基本的原理,是最基础、最质朴的东西,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离开这些理论,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还是更进一步延伸,都和这些理论有关。你很难完全抛开这些基本的东西去研究,因为那意味着否定了经济学本身的存在。所以,从发展的意义而言,译旧显然不如译新。那些新的研究、新的著作,更需要翻译的支持,它们是从经典中来说,同时也和现实直接相关,我们已经有了经典,但现在我们缺乏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