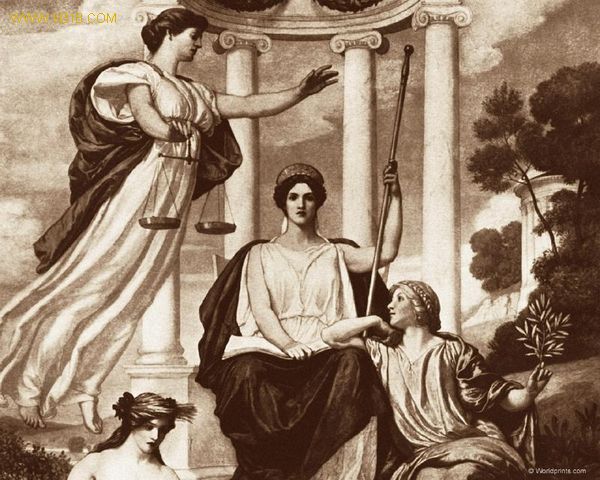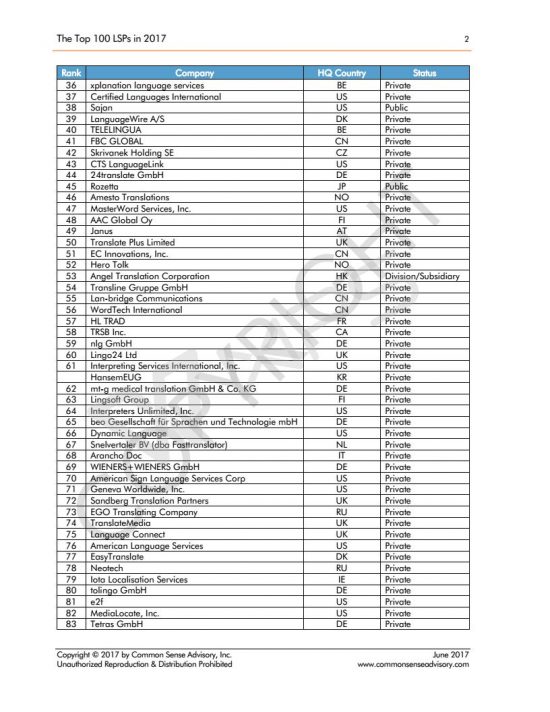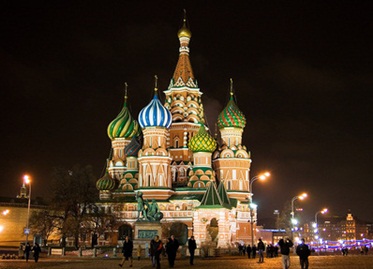周作人对于希腊神话的热心,是众人皆知的。他生前共翻译了两种希腊神话,第一种是英国人劳斯(W.H.D.Rouse)所著《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Gods,HeroesandMenofAncientGreece)。此书出版于1934年,周作人在1935年2月3日的《大公报》上就已撰文予以介绍。不过,在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并没有翻译它的心思,因为嫌它是用英文写的儿童读物,并非希腊神话专门之书。直到1947年,周作人觉得它毕竟是英美人所作同类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兼又爱好其人其文,故花了两个月时间,将它译成中文,经友人介绍交给了一家出版社,可是不久遇火被焚。1949年又重译,1950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题为《希腊的神与英雄》。1958年,又改题《希腊神话故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海南出版社于1998年重以《希腊的神与英雄》为名出版,无任何出版说明,当系文化生活版的再版。此书很好读,书后附有周作人有关希腊神话的几则随笔,颇可参看。其中《在希腊诸岛》一篇译文,不仅描绘了今日希腊飘漾着神话气息的民俗风情,而且文笔清新摇曳,尤有情致。
第二种为阿坡罗陀洛斯(Apollodorus)的《书库》(Bioliotheke),此书极受周作人的重视,因为它是希腊神话原书仅存的两种之一。周作人在《希腊神话二》中引用了英国人俄来德(F.A.Wright)《希腊晚世文学史》对《书库》一书的介绍:“我们从文体上考察大抵可以认定是西历一世纪时的作品。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七卷书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从罗马的伐谛冈(即梵蒂冈)图书馆里得到全书的一种节本,便将这个暂去补足了那缺陷。”事实上,周作人也正是受了Wright的启发,才于1934年发心翻译此书的,所用底本为勒布古典丛书本,有弗来若(Frazer,今译弗雷泽)博士“上好的”译注。据周作人写于1944年的《〈希腊神话〉引言》中说,在1937-1938年间,他为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翻译此书,“除本文外,又译出弗来若博士《希腊神话比较研究》,哈利孙女士《希腊神话论》,各五万余言,作本文注释,成一二两章,共约三万言。”后因该编译会迁至香港,故译事中辍,已经译好的稿子也被编译会带走而下落不明。1944年,周作人又有心重续旧译,所以先将已译的原文及部分注释以《希腊神话》为题连载于《艺文杂志》,并为之作了上述“引言”。可是仅连载了三期(第十至十二期)即告终止,周氏的续译计划也并未展开。解放后,出版总署叶圣陶等希望周氏能翻译一些希腊作品。于是在1950-1951年间,周氏在译完《伊索寓言》后,即又重新翻译了这部《希腊神话》,原文与注释均已译毕,但交付出版的情况,很是不明。《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这希腊神话的译稿于完成后便交给开明的”,可是《知堂回想录·北大的南迁》中却说这部译稿“原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因为纸张的关系,尚未刊行”。不管怎样,此书在周氏生前,终于未获出版。
其实,周作人是极为看重自己翻译阿氏《希腊神话》的工作的。他在《〈希腊神话〉引言》中说:“我以前所写的许多东西向来都无一点珍惜之意,但是假如要我自己指出一件物事来,觉得这还值得做,可以充作自己的胜业的,那么我只能说就是这神话翻译注释的工作。”1965年4月26日,周作人曾写过一份遗嘱,后来又专门补上了这样几句话:“但是阿波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版,则亦是幻想罢了。”更可见出周氏耿耿于怀的执着与巨憾。
现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了一个《苦雨斋译丛》,其中就收了周作人的这部《希腊神话》译稿。此书的面世,距周氏之弃世,已有三十余年,距此译稿的完成,也已近半个世纪,至于距离周氏对此书的第一次翻译乃至其初发心愿,更是荒忽兮辽远,这或许也可算是本世纪中国文化界许许多多徒资唏嘘的人事之一例吧。从这意义上说,我们对出版此书的中国对外翻译公司以及总领其事的止庵先生深表敬佩。
不过,出版者似乎也仅满足于将此译稿公诸于世,对译稿的情况、周译的过程以及其中的问题未作细致的耙梳,所以留下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遗憾。比如止庵先生附于书尾的《关于周译〈希腊神话〉》介绍周译的过程说:“此后将近二十年里,他先后把这书翻译了三次,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是第一次……译稿后来被文化基金编译会遗失了;一九四四年是第二次,连载于《艺文杂志》,只登了一小部分即告中止;一九五一年是第三次,即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书……”可是,周作人实际上只译过两次,见上文介绍,周作人本人在各种场合谈到其《希腊神话》的翻译时,也都只说译了两次,别的且不例引,便在此版《希腊神话》的书首,收录了周作人作于1958年的一篇引言,文中就明确写到:“本书翻译凡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第二次是一九五零年,这是第二次的译本。”止庵先生将周作人的第一次翻译误认为两次,以为第一次译稿既已被文化基金编译会带走,所以1944年周氏刊登在《艺文杂志》上的便是另一种重译稿。事实并非如此,在周作人写于1944年的《〈希腊神话〉引言》中,再三说原文已经译好,注释还差17章,非得自己亲自完成不可。其在《艺文杂志》上连载的过程与目的则是:“现在先将原文第一章分段抄出,各附注释,发表一下,一遍抄录过后,注释有无及其前后均已温习清楚,就可继续做下去,”这里两次用“抄”字,可见当时周氏手边仍有译稿,所以他接着并说“我的愿望是在一年之内把注释做完”,而不是全部重译。从这些文字我推想其翻译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周氏先将阿氏原文译出,又翻译了弗来若博士、哈利孙女士的有关论述,这是底稿;再将这些论述分别安插到原文各章节作为注释,重新誊抄后即为正式稿,当初只配好了两章,就被编译会带走了。但底稿应该还在周氏手边,所以1944年发表时,他一边将原文“分段抄出”,一边又将相应的注释配好,这样“抄录过后”,才能“温习清楚”,以便“继续做下去”。这样的推想与实际情况到底出入多大很不好说,但总之周作人只翻译过两次《希腊神话》,当是无可置疑的了。止庵先生称周作人曾翻译三次,未免过于轻率。
此外,还有几个小问题需要略加说明。其一,《〈希腊神话〉引言》说:“《希腊神话》,阿坡罗陀洛斯原著,今从原文译出,凡十万余言,分为十九章。”文中又说十九章原文均已译好,注释才做了两章,“还有余剩的十七章的注释非做不可”。可是此版《希腊神话》首分以卷,卷下分章,章下分节,并无全书分为十九章的任何痕迹,只有书前所附华格纳耳(Wagner)所编的《纲要》,才是将原书四卷依情节性质又分章的,但他是分为十六章,周作人所据底本是弗来若的注释本,其中也不过移录了Wagner的《纲要》而已。周作人的“十九章”之说,若非Wagner“十六章”之误,究竟另有何据,则不得其详。其二,周作人《希腊神话二》(1934年)及《〈希腊神话〉引言》(1944年)都引用Wright《希腊晚世文学史》中介绍阿氏《书库》的一段文字,其中说:“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们遇到雅典诸王,德修斯在内,随后到贝罗普斯一系。”从今版周译《希腊神话》中可知,原本第一卷共九章,原本第二卷共八章,原本第三卷共十六章,节本共七章。第二卷共才八章,哪来第十四章呢?只有第三卷中有第十四章,从Wright所述内容来看,的确指的是第三卷第十四章及其后面诸章,所以“卷二”当为“卷三”之误无疑。周氏之文原刊如此,或为周氏笔误,今各种周氏文集均仍其误,非独苛责本书编者。其三,阿氏身世虽不能详考,但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他是公元一世纪之人,周作人常称引的Wright与弗来若亦均主此说,所以周作人在前此的文章中也这么认为,《〈希腊神话〉引言》开首明言:“著者生平行事无可考,学者从文体考察,认定是西历一世纪时的作品,在中国是东汉之初,可以说正是扬子云班孟坚的时代。”此版《希腊神话》首附周作人写于1958年的那篇《引言》却说阿氏乃是“公元前一世纪”人,距离公元前五世纪的前辈斐瑞库得斯(Pherekydes)“要迟四百年”,这是明显的记忆错误。止庵先生对此版书首引言未加任何说明,或限于资料不足,无可厚责,但对于这样明显的失误,作为总其事者,还是有必要细致阅读并加以说明的。甚至,止庵先生“原本是爱读书的人”,又深信出版此书“也会是天底下读书人之所同好”(止庵《〈苦雨斋译丛〉总序》),那么对于周氏译稿的辗转经过多作些交代、对于上述所及的各项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与说明,或也可说是责无旁贷的,何况这也并非难事,不过多费些工夫罢了,原不必非“要多长一点学问,至少也要学会希腊、日本两门外语”(止庵《关于周译〈希腊神话〉》)才做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