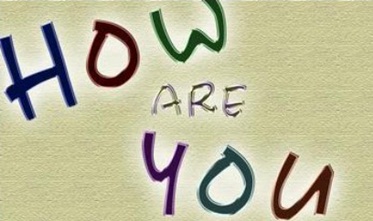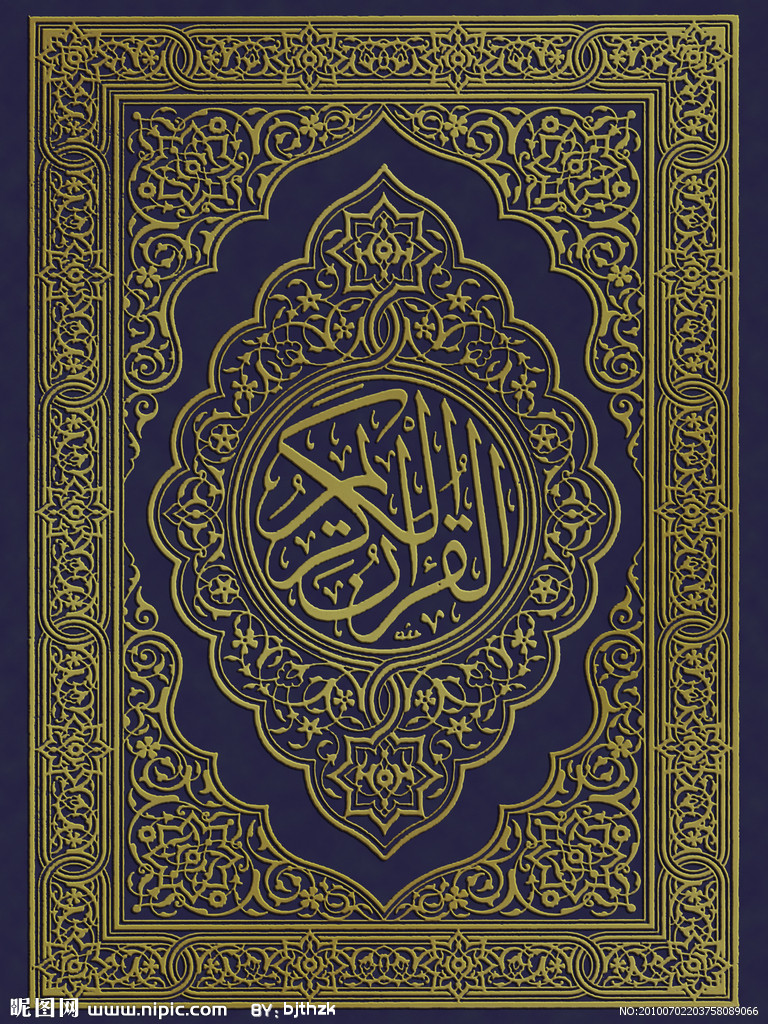这个世界的大多数科技精英,会把其能力转化为个人财富和社会声望,而“维基解密”的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则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是个怎样的人?有过怎样的经历?他在追求什么?译林出版社近日出版,由常江、任海龙两位译者翻译的《阿桑奇自传》以自述的形式揭开了阿桑奇的秘密。
常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译著有《在华五十年》、《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媒介经典文本解读》等,著有《帝国的想象与建构:美国早期电影史》,为《阿桑奇自传》译者之一。
翻译是良心活,需要真诚、不计回报的付出
问:为什么接手《阿桑奇自传》的翻译工作,是什么吸引了您?两位译者是怎样分工的?
常江:译林出版社的何本国老师联系我,问我是否愿意翻译阿桑奇的回忆录。此前我翻译过几本书,多为学术著作,非学术类书只一本,也是回忆录——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
外人也许不知,翻译在国内是极其辛苦、报酬极其微薄的工作,基本相当于义务劳动。我会答应翻译一本书,通常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书的学术价值高,将其译为中文,有助于我的同僚和学生学习、研究;二是书的内容十分重要,对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议程有显著的揭示作用。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和阿桑奇的回忆录,就属于后面这种。这类文献极其重要,关涉人们对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理解,因此如果落入不负责任的译者手中,将是知识的重大损失,所以我才会答应。当然,我也同时提出希望和任海龙老师合译,这样能在确保译本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我和海龙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合作方式也很灵活,没有一个简单明晰的分工。但从工作量上看,他承担的内容比我多。
问:阅读时感觉这本书流畅、本土化,没有所谓“翻译腔”,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吗?
常江:首先感谢谬赞。这与我们的经历和专业有关。海龙和我是北京大学校友,他在英语系接受了系统的语言文学与翻译的训练,后又在联合国劳工组织等机构做过专职翻译,是国内最出色的译者之一。我是搞新闻传播学的,阿桑奇与维基解密及其对全球信息传播系统、权力监督机制产生的影响,是我的专业范畴。同时,新闻系出身、新闻学院任教的我,历来崇尚朴实、流畅的文风,反感炫技式的花哨与华美。 我们的配合可以算是天衣无缝。当然,我们两个都是有丰富的翻译经验的“老手”,分别出版过四五本译著了,对于技术和细节问题,早已轻车熟路。
这里多说一句吧。其实“没有翻译腔”谁都能做到,一点也不难。通常,多做两遍校译,把别扭的语句好好顺一顺,基本就没问题了。中文是我们的母语,难道母语怎么说顺溜还用别人教吗?翻译是良心活,需要真诚、不计回报的付出。我们两个都各有繁忙的工作,但愿意拿出时间来真诚地做这样一件事,是出于对书籍文明的敬畏之心。我听说现在很多书都是用软件翻译的,难怪文句不通,令人齿冷。
问: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否存在专业术语上的障碍?
常江:似乎没有遇上什么特别的障碍,因为英文原文本身也并不晦涩,比较流畅。专业术语我这里都能解决,实在不行,现在信息检索手段这么多,也能很容易查到。倒是附录部分(指解密文件)费了些工夫。我们以前都以翻译学术著作为主,佶屈聱牙的英文见得多了,翻译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反而很享受。
阿桑奇本人的声音,是对其的种种阐释中一种必需的平衡
问:您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哪里?翻译过程中对哪部分印象深刻?
常江:阿桑奇和维基解密,从出现在大众视线中那一刻起,一直是被观察、被阐释、被批判的对象。大众、媒体、政府、商业机构,莫不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赋予阿桑奇和维基解密以种种意涵。但是阿桑奇的声音在哪里?他如何诠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他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评价?我想,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给这个出于种种原因无法和世界进行直接沟通的男人一个系统发声的机会,它让大众有机会倾听阿桑奇用属于自己的语调和声音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是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必需的平衡。
给我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全书的开头,阿桑奇记录自己在监狱中的感受和思考。这些感想和思考,可被视为其价值观的一个全方位的总结,很令人信服,也很动人。一个视自由为生命的男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做何感想?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问:序言中谈到,阿桑奇签订出版合同之后又反悔,说“写回忆录像卖淫”。这本书真的暴露了他很多隐私吗?
常江:按照现在人们的“尺度”来看,书中真的没有什么不宜披露的隐私。读过全书后,你就能感觉到,阿桑奇是一个在内心深处对外部世界极不信任的人。有此反悔,并不令人意外。
问:您认为书里呈现的阿桑奇真实吗?他是怎样一个人?
常江:我如何认为并不重要,是否真实、多大程度上真实,只有阿桑奇自己知道,哈哈。我是翻译,是意义的搬运工,不制造新的意义。既然是“自传”,意味着很多信息缺乏交叉信源的验证,可能会有对事实的夸大或错述,本书也是一样。
总体上,阿桑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自由主义者,这当然与他成长的环境有关。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就游走于体制的边缘,不但积极参与各种抗议活动(如反战),而且对很多传统价值观(如婚姻、家庭)不屑一顾。他从小就和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且不断为“主流人群”所排斥。书中有一个细节,讲述他和母亲的老房子失火,消防车来得很晚,邻居也多有幸灾乐祸之意。类似的经历,强化了他的极端自由主义价值观——甚至已经可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他蔑视权威,并先天将一切机构视作个体的敌人。
维基解密的意义在于宣告被确信的事物有可能是可疑的
问:在书中阿桑奇提出,网络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实质的言论自由,反而给信息强权部门侵犯个人隐私的便利。对此您怎么看?
常江:网络无论有多么无远弗届的威力,终究只是人类发明,并为人类所用的工具。它所发挥的作用,自然既有可能是解放性的,也有可能是破坏性的。因此,我不赞成剥离开人和环境的因素去孤立地谈论媒介的功能。就像直播卫星的发明让新闻传播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力,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却也为军事机构作侦探、窃听之用一样。在客观上,网络究竟更多发挥了解放性的作用还是破坏性的作用,也是因时、因地而异的。至少在中国,互联网大大拓展了言论自由的边界,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问:阿桑奇、斯诺登这样的解密者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他们是否应该被视为英雄?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
常江:尽管阿桑奇和斯诺登两人做的事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他们在本质上并非同一类人。在我看来,斯诺登的行为是出于较为朴素的正义感。他本人曾是中情局雇员,他的揭秘行为也仅止于自己的前东家。对他来说,也许这是实现“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而阿桑奇则不同,他的“维基解密”在本质上针对所有机构(包括政府和商业机构)。对于阿桑奇来说,戳穿这些机构的神秘面纱是一种本质的生活方式。
至于他们是否应该被当作英雄,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就如同孔夫子到底应不应该被尊为“圣人”呢?恐怕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想,这才应该是我们理解维基解密的关键所在: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一切被确信的事物都有可能是可疑的,在于为人们观察世界、阐释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或许永不会成为“主流”,却会一直以令“主流”头疼的方式,在人类社会变迁的某些关键的节点上,熠熠生辉。(采访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