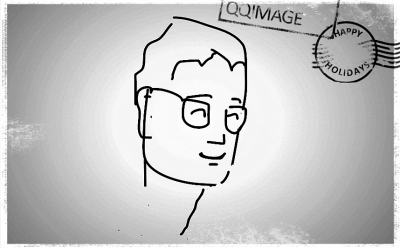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世界空间是由具体的“外语中国”所构成的,没有某一语种的“中国文化”馆藏,就很难有具体外国的“中国文化”。
·文化弈局·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就学术传播论,当以严复引领风气;以文学翻译论,林纾则无疑拔得头筹。但事实上文化流播轨迹并非完全的“一边倒”,文化交流正是在互动意义上才显示出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如此,考察欧洲(乃至西方)的东方接受,尤其是中国文化播传德国之过程,思想翻译固然重要,文学翻译对西人认知中国则更有实证的意义。
德人查赫以学术性的中国文学翻译蜚声学界,但学术意义远过于普及功能;库恩则正相反,他讲究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自其从导师的“毒柜”(存禁书的柜子)找到了“奇书”《卖油郎独占花魁》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建构起了一个“德语世界里的中国文学殿堂”,不仅为一般德国民众喜闻乐见,亦对高等知识人的中国修养形成(包括汉学家)颇有助益。
作为西方最早的《红楼梦》译者(节译本),库恩译本的文化影响甚大,曾经多次重印,并被转译为英、意、荷等其他语种。除此,还有《金瓶梅》、《水浒》等无数中国文学名著所构建的库恩德译“中国文学”。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世界空间是由具体的“外语中国”构成的,没有某一语种的“中国文化”馆藏,就很难有具体外国的“中国文化”。
同样,当近代西学东渐之际,以文学论,“林译名著”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标志。后来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周氏兄弟等,都曾回忆过林译名著给予他们潜移默化之影响。相比较严译名著主要集中在思想学术方面,林纾不通外文,但却能借生花妙笔与口译之助,构筑起外国文学汉语世界的“林译殿堂”。
林纾本不谙外文,宛如“盲人摸象”,却列身于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家行列,说起也有偶然性。当年林纾新鳏,心情不愉,坚拒名妓的青眼有加后,为驱孤寂,与福州船政学堂的诸君来往颇密,如魏瀚、高而谦、王子仁(寿昌)等,他们都曾留欧,所以无形中帮林纾打开了面向西方的另一只眼。朋友郑叔恭为他在巴黎代购了法文原版的《拿破仑第一全传》与《俾斯麦全传》,他对传主兴趣极大,但不通外文,只能望洋兴叹;求之友人翻译,终难快意过瘾。最后,以王子仁口述、林纾文言笔述的方式进行合作,再加魏瀚的鼎力相助,终获成功。
还有,幸遇《茶花女》这样契合林纾当时心境的书,引发其全身心的情感投入,乃至“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丈夫。”(见孔庆茂:《林纾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正因如此他才能“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由此开端,译出《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名著,以达“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的目的。
如果说,林纾的成就在于“化为我用”,他在中国语境里成就了“林译外国文学殿堂”,表现的是如何将外来文化资源善加整合的问题;那么,库恩的中国文学德译事业,则应放置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于世界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每一个主要的外国语种,都能产生库恩这样的“中国文学”翻译家,那么中国文化的融入世界,就真的不再是“望梅止渴”之梦。而经由文学对中国的认知,则无疑更可让世人洞察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所谓“中国威胁论”自然也就会烟消云散。正如歌德经由《玉娇梨》、《好逑传》所认知的中国未免不够丰富,却为一流知识精英提供了“窥一斑而知全貌”的可能。
设若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能有所作为,则内可“自固根本”,外亦可“游刃有余”,那么中国思想的原创性也就水到渠成。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出现,也就为时不远,撒切尔夫人冷嘲中国是只出口物质产品的“大国”类言论,也就自然不足为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