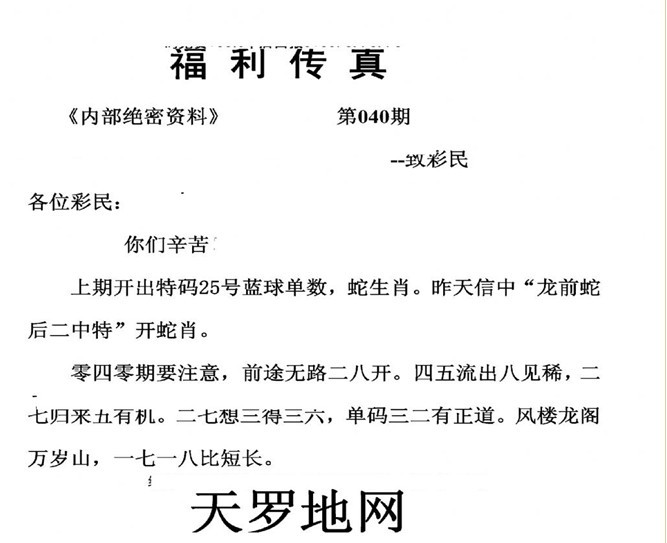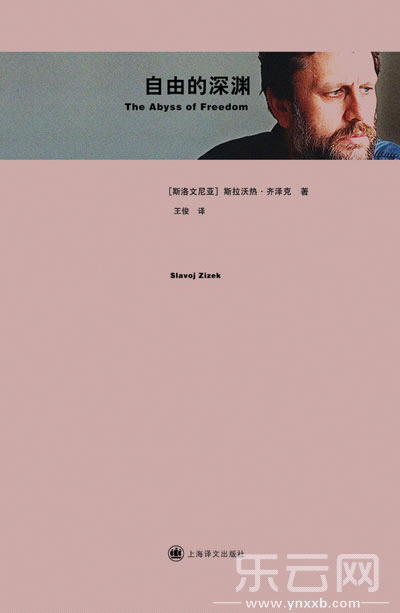高莽,1926年生,哈尔滨人。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长期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其所属单位工作,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 编。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有《久违了,莫斯科!》、《灵魂的归宿》、《圣山行》、 《俄罗斯美术随笔》、《文人剪影》、《心灵的交颤》等;译有《保尔·柯察金》、阿赫马托娃长诗《安魂曲》、鲍· 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体自传《人与事》等;在绘画方面,画过许多文学家肖像画,为国内外文学馆、纪念馆所收藏。曾获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称号、俄罗 斯作家协会“高尔基奖”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授予的“友谊”勋章。

翻译生涯多难又多彩
1943年,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刊出了高莽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他开始了多难又多彩的翻 译生涯。抗战胜利后,高莽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翻译了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由此也找到了终身的爱人孙杰。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样走上翻译道路的?
高莽:我在学校没学到过中文,但我从事翻译工作挺早。我非常欣赏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觉得很美。1943年,我17岁,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读了他的散 文诗,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其实远不理解该诗的深层含意。我认为能看懂,拿起笔能用汉语写清楚,就算是能翻译了。可翻译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越到后来越 觉得不简单。我是越来越不敢翻译了,因为觉得看着文字都懂,可文字深层的东西就体会不出来。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剧本也好,这些文字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这方面我有很多教训。
南方都市报:有什么样的教训?
高莽:那时候觉得能看懂俄文作品,能把作品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就是翻译成功了。投稿,发表了,得意洋洋。直到后来翻译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 编的剧本才发现了问题。那是1948年,剧本中全部是人物对话,对我而言翻译对话比较容易,因为我小时候跟俄罗斯同学们讲话一直用俄语。剧本翻译好了,在 当地演出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这部话剧时,发现里面有不少东北土话,尽管编导已经改了很多,但仍有东北腔调。这时我才明白:语言 是种艺术,搬上舞台更要注意语言的文采,外国剧本不能变成中国地方戏。
南方都市报:后来如何提高自己的水平?
高莽:1947年,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三十周年,举行了一次苏联图片展览,参观的人很多。从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看 过之后说我翻译的图片说明语言不纯。我知道自己中文功底薄弱,但没有想到语言的纯与不纯。这件事情给我敲了一个警钟。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阅读中国著名作家 的作品,不仅读,而且还琢磨和研究遣词造句,并开始有意识地注意表达方式。
1951年我出版过一本译著:《龚查尔短篇小说集》。“文革”结束以后,我把这本小说集补充了一些篇章,再次出版。有一位女编辑看了以后,说:“高 莽,你的文字三十年没有进步。”我一想挺奇怪,我一直搞文字工作,怎么还说我没有进步呢?她指出我用词造句方面的毛病,译法缺少技巧,文字缺少时代感。于 是我专门认真学习我们一些老作家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经验,他们是怎么理解原著,怎么进行翻译,怎么运用汉语来表达原文精神的。1979年我收到巴金先生 的一封信,他说:“您的俄文好,中文好……”“为什么不同时译几本沙俄小说呢?”我所崇拜的老作家对我的鼓励和文学的肯定,让我由衷地感动和欣喜。我更意 识到文学事业上无坦路,今后需要更加努力。
南方都市报:1948年,翻译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高莽:那时候我在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因为我会俄文,追求进步。中苏友好协会下设有书店,有电影院,有合唱团,有各种文艺组织。我什么都参 加。我还管理过友协的俄文图书,那些图书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给友协的。有一天我发现有一部剧本叫《保尔·柯察金》。那时我还没看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我一看那个剧本,很震惊:天下还有保尔式的人!完全崭新的一个人物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从年轻的时候献身革命,为人类解放事业进行艰苦的斗争。他当 过工人,红军战士,打过仗,负过伤,身体残了、眼睛瞎了,还坚持革命事业。我看过剧本以后,就非常喜欢保尔这个人物。我把剧本译成了中文。我当时没有任何 其他打算,也没想到这是一部特别有影响的著作,纯粹由于喜爱。我的译文很快印成了书。哈尔滨教师联合会文工团有人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决定演出。演出非常 轰动,因为这是在中国大地上演出的第一部革命作品。当时大街小巷都在谈论保尔,哈尔滨青年掀起了学习保尔的高潮。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翻译工作中,戈宝权先生给了你很大的启发?
高莽:戈宝权先生是我的前辈,我的师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派戈宝权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他路过哈尔滨,看到哈尔滨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 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他特别细心,就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要跟大家交流交流。我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 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他说:“你们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啊?约好了时间开会怎么没人来?”我就问他还有哪些人,他把本子掏出来给我看,又把人 名读了一遍。我说人都到齐了,因为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不想做翻译。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这个印象很深。我怎么能去干这个职业呢?可是我自己又喜欢俄罗 斯文学,又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以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宝权先生。他讲了一些道理,然后概括成两句话,大意是:关键看我翻译的是什么东西,是为谁翻译 的。这两个问题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翻译?之后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笔名就改成了“乌兰 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绘画爱好相伴一生

马克思与恩格斯 图/高莽
文学翻译和创作之外,高莽还从事绘画。他说:“绘画是伴我一生的业余爱好。”1949年,高莽创作的讽刺漫画受到批判,华君武曾对他说:“我扼杀了 一个漫画家。”他则说:“你救了一条人命。”而后,高莽着力于肖像绘画,其中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肖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 基、巴尔扎克、井上靖等人的肖像为国外文学馆或纪念馆收藏。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迷恋上绘画的?
高莽:我从小就爱画画。我记得小时候看小人书,根据小人书上的人物画出来,再一个个剪下来,摆成一排,调换地位地玩。后来跟俄国老师学画,先后跟过三位老师。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画过漫画,还出了事?
高莽:我画过漫画,那已是快六十年前的事了。华君武、蔡若虹还批过我。1949年,我为哈尔滨市青年团《学习报》画了七幅反浪费的漫画,刊出四幅。 开始大家都反映挺好的,后来不知哪位同志写信给市委宣传部说:那些漫画是丑化人民,画的作者思想立场有问题。开始追究责任,把我给拉出来了。新中国成立 了,《文艺报》根据那封信开了研讨会,委托华君武、蔡若虹撰文批判我。《文艺报》从第一版到第八版都是批我的,还有我的检讨、报社的检讨、读者的来信,并 附了我的四幅漫画。所幸那时候是刚解放,批得还不厉害。从那以后我学乖了,再也不画漫画了,若讽刺就讽刺帝国主义。我跟华君武关系一直很好,他跟我说: “我扼杀了一个漫画家。”我说:“你救了一条人命。”要不然的话,凭我那点小聪明,一直画漫画的话,肯定会出大问题,那些运动里面我不去画漫画才怪呢。
南方都市报:受了这次教训之后,画风有没有变化?
高莽:受了批判之后,我再也不画漫画了,再也不进行讽刺了。我只画美化人的作品,歌颂性的作品。记得我母亲说过:“画男人要画年轻一些,画女人要漂 亮一些。”她的话非常灵验。凡是按她的标准画的肖像,都会得到好评。但有两位大学者对我说:“按你母亲的要求作画,不会有好的作品。”他们的话很有分量。 美化现实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文革”期间,我们下放到农村,除了马恩列毛的作品,其他什么书都不让看。偶然一个机会我得到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回忆 录。我发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人情、亲情、爱情,而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得什么情都没有了,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时代。这些感触促使我通读了马恩著 作,并画了马恩两家人,后来扩展到他们的战友们,他们的事业。我当时想画五十幅,因为身体不太好,我估计只能活五十岁,结果画了五十七幅,看起来还能多活 两年。我在干校里躲着在蚊帐里画。回来后接着画,一共画了七年,画完了以后给美术出版社的人看,他们说好,就给我出版了。后来我较多地画了作家肖像,特别 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几十年来,回头一看,都没想到自己画了那么多肖像,仅中国的作家,有他们签名的,我就画了二百多位,画俄罗斯作家的也有一百多幅。
南方都市报:你原来在学校接受的是俄罗斯的绘画教育,后来对中国绘画又有新的认识,这对你的绘画有什么影响?
高莽:我十几岁开始学画油画,画了四十多年。后来我妻子对油画颜料突然过敏起来,我就抛弃了油画,开始画国画。这时我才慢慢了解国画的深奥。中国的 笔墨纸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画国画必须要有很深的文化根基。有一位外国画家朋友来了,想试试用毛笔作画,不行,一抹就是一片黑。中国画超越了焦点透视、阴暗 等,没有足够的中国文化修养,是画不好国画的。我在这方面有很多欠缺,我在努力学习。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