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保胜
人民日报5月22日有篇文章《糟蹋好书》,是谈翻译的“胡译”“乱译”的,说的是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战后欧洲史》,“全书中错译、误译、张冠李戴、人名地名不规范的地方俯拾皆是……糟糕的翻译糟蹋了一本好书。”比如,将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译为和瑞典交界处,而法国与瑞典隔着德国和波罗的海,真不知它们如何“交界”。又把英国威尔士的城市Swansea,所有大陆版地图都音译为“斯旺西”,英格兰超级联赛中有这个城市的球队,新华社译为“斯旺西队”,这本书却自作主张地把这个城市意译为“天鹅海市”。文章举出了不少荒唐的错误,简直不忍目睹,“这些年粗制滥造的翻译书很多,但像《战后欧洲史》这样过分的还真不多见。93万字的两册书差错多得数不过来。”
看完这篇文章,我也叫苦不迭,大呼上当,买的这套书还没看,看来是没法看下去了。这篇文章的作者还能勘误纠错(他自称只是一个普通历史爱好者,不是专业校对,却都挑错挑得目瞪口呆),我等要是对欧洲历史不甚了解的,要想靠它了解战后欧洲史,看来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了,这样的书不是害人吗?要信了它,不知以后要出多少洋相,丢多少人,想想都胆寒。作为读者,我们都这样害怕学到谬误丢脸出洋相,那些专家学者,那些出版社,他们就怎么那么大胆、那么好意思不怕寒碜呢?
买书遇到这样胡乱翻译过来的东西,既糟蹋原书,又浪费读者的金钱和精力,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满盘皆输。连个冤都没处喊,只能自认倒霉。
而翻译的书粗制滥造、错讹百出,已是屡见不鲜了。前几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费正清翻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翻译成林海青;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翻译成赫萨,海外近代史大家徐中约被译成苏春月等等。尤其是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是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孟子”被译成“门修斯”之后出现的又一人名翻译大错。一时舆论哗然,当年媒体上有不少报道。
关于翻译好坏的争论也非今日才有,早在1929年,梁实秋发表《论鲁迅的“硬译”》,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来回击。在梁实秋与鲁迅就“硬译”大打笔墨官司时,当时复旦大学的教授赵景深也出来发表意见了,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赵景深的“宁达而不信”的论调客观上呼应了梁实秋的主张。
后来鲁迅有诗《教授杂咏》道:“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这是鲁迅戏谑赵景深的。赵教授曾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国外文坛消息》,介绍德国作家的作品,却将《魔鬼》译成《健身》,把《半人半马怪》译成《半人半牛怪》。他还在契诃夫小说《凡卡》中将英文MilkyWay(银河)误译为“牛奶路”。鲁迅指出:像赵景深这样“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可见他的“宁达而不信”,实际上是主张“乱译罢了”。
现在一些国外名著,动不动就几个甚至十几个版本,大多都是质量平平,甚至是“迢迢牛奶路”、“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译得不堪卒读文理不通。当年,朱生豪先生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其在中国近代英译汉历史上被称为划时代的译作。他在20岁之前就选择了莎士比亚,潜心钻研,放弃了自己写诗写文章的爱好,“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穷其短短一生心血,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也因此,至少像我这样不懂外文的人,才有福领略到莎剧的神韵和魅力。而莎士比亚能在中国遇上朱生豪,又是何其幸运。
而今那些动不动就以“神速”“乱译”出来的书多如牛毛,几十万字的书,人家一两个星期就“译”出来了。据说,不少学校的教授像包工头做项目一样,拿下项目,再找几个学生“分包”,三下五去二,就“翻译”了,最后署上教授啊专家啊之类的大名,让读者有一种“望名山而拜”的想法,舍得掏腰包,“翻译家”则名利兼收。殊不知,这样偷梁换柱、挂羊头卖狗肉,敷衍塞责出来的译作,让读者像吃苍蝇一样。如是再三,读者还敢轻易买译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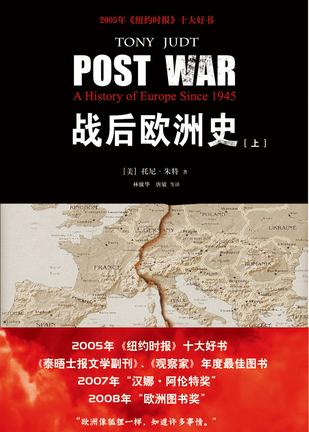
战后欧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