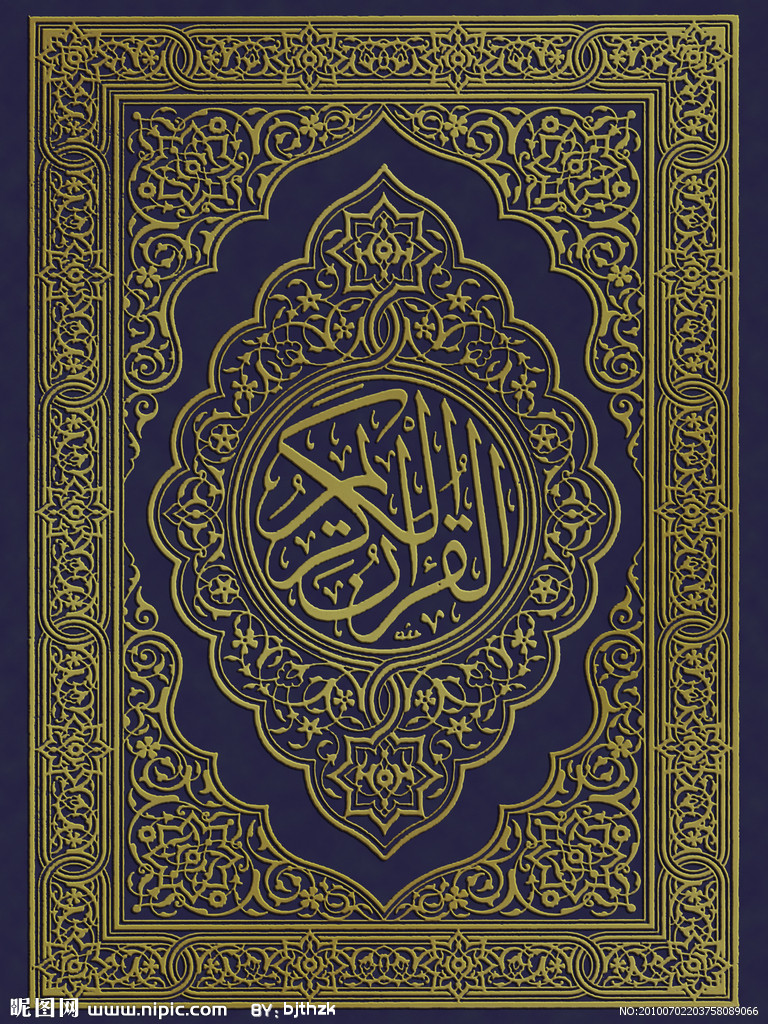“西学东渐”一词最初见于容闳1915年出版的英文传记中译本《西学东渐记》,后被用来泛指晚清以来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盛行的历史过程。
历史上,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虽发端于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但严格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应是起于洋务运动时的晚清时期。其外在形态就是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想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内在标志就是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开始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来源。从明末发端到晚清民国形成气候,西方文化思想的东渐在中国思想界先后经历了拒绝抵制、逐渐接受、全面吸收的历史过程。整个西学东渐的过程,正好是近代中国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受到不断拷问质疑的过程。因而人们往往耿耿于晚清以来的西学得以东渐,东学却未能西进。个别甚至把西学之所以东渐简单归结于自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有意识的文化输入;把东学未能西进认定为由于语言障碍,国人中缺少一批像西方传教士一样的人,有意识地把中国的学术典籍译介到西方,使得西方各国对浩繁的中国经史典籍、文化思想缺乏了解。
然而事实则不然。只要我们细心搜寻历史,不难发现:明末清初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不仅带来了《乾坤正义》等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也将中国众多经史典籍带回西方,并被各国纷纷译为本国文字,加以研究。只是当时传教士们的活动十分有限,传教之余带入的西方著作多限于《乾坤正义》《坤舆万国全图》等天文地图数学著作;加之后来乾隆的禁教,并未广泛流传,更未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想来源。真正促使西方学术文化著作的大量译入,使西方文化思想成为影响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想,恰恰是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马建忠、张元济等中国有识之士自觉的传播力行。
目睹洋务运动的逐渐破灭,严复、马建忠等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为求富强,抵御外辱,单有洋务是不够的,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放弃“西学源出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固有思想,认真学习导致西方各国富强兴盛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改变当时中国民力已弱、民智以卑、民德以薄的客观现实;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把中国导向富强。为此,马建忠在1894年发表了著名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以其多年出使法国、英国的经历告诉国人:自明朝海禁开放以来,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早已将中国的经传典籍等译为拉丁、法、英等文字。还在康熙年间,法国巴黎就开设了汉文馆,专门从事各种汉语著作的翻译。“近则各国都会,不惜重资,皆设有汉文馆。有能将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小说,译成其本国语言者,则厚廪之。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尽通其底蕴不止。各国之求知汉文也如此,而于译书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进而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屡屡受欺于人,就在于闭关锁国,不通外文,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处处受制于人。认为,自“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睨于京师,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力主效仿西欧各国,设立专门的翻译书院,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广泛翻译西方各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科学著作,以便知己知彼,学习西方各国之长,补己之短。马建忠希望设立的翻译书院,是借鉴西方各国开设汉文馆的经验,全面学习翻译西方各国的政治文化典籍,而不同于洋务时期,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开设的译署。因为,在马建忠看来,“今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与京师译署,虽设有同文馆,罗致学生以读诸国语言文字,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译专书,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意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其律例公法之类,间有摘译,或文辞艰涩,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或挂一漏万,割裂重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
可以说,自李鸿章、张之洞等朝廷重臣主政洋务以来,虽然大兴洋务,效仿西方各国兴办船政、矿务、电邮、铁路、海军、学堂、译署等,但因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洋务运动始终重在对西方各国具体军事工业技术的学习,而非孕育现代西方社会工业文明的科学与民主宪政思想,以致洋务运动始终在西方各国后面亦步亦趋。其洋务本身,无论是借鉴西方各国开办的各种实业,还是兴办的水师、学堂、译署、同文馆,不是借椟还珠,徒有躯壳;就是未得要领,大多落入官僚资本的窠臼,其强国梦最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破灭。针对洋务运动的失败,一批深受西方思想浸润的学人重新开启了学西方的思想历程,直接催生了戊戌变法、预备立宪等政治变革。虽然无论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的预备立宪都同洋务运动一样,未能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权力制约,最后都未能挽救清朝的衰败覆亡,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此兴起的对西方思想的学习和传播,却有增无减,各种西方思想纷纷被译介到中国,使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
引进输入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就翻译传播而言,马建忠、严复和林纾功不可没。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幕僚,生于内忧外患之时。1853年因太平军攻陷南京,随家迁往上海,进入设在徐家汇的耶稣教会徐汇公学读书,开始学习法文、拉丁文等课程。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促使马建忠毅然决定放弃科举之路,专心学习洋务。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自称“于汉文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实、舆图、政教、历算,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博览西方文化科学典籍。不仅精通西方语言文字,而且长期出使海外,先后随清朝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多年。特殊的经历使他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审视东西方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他率先提出设立翻译书院,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全面完整地翻译西方典籍,开风气之先。严复不仅同马建忠一样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学贯中西,主张全面完整地翻译西方政治文化典籍,全力驳斥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谬性,主张体用结合的西体西用。他认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深信只有推行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废除中国的封建礼俗思想,采用欧美的宪政体制才是改变中国贫弱的出路。严复不但身体力行地翻译了赫胥利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自由论》)、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富论》)等西方思想文化的经典著作,引领社会;就是当年在《天演论・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至今仍为学界遵奉,无人可以替代。林纾虽不懂外语,但借助别人口译的方式先后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170多部西方各类小说,对广大民众全面了解西方社会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普及作用,使中国大众对西方社会文化有了第一次全面的了解,是把西方文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对后世影响甚深。如钱锺书就说,他是从看林纾的翻译小说走上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的。
渐这一历史过程中,张元济也是一个功不可没的历史人物。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张元济也是出身科举的维新人士,早年参与了戊戌变法。只是思想上张元济持有类似严复一样的思想,认为变法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事,关键在于开启民智,主张专办学堂,讲求种种学术,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用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取代陈旧落后的旧思想。他目睹戊戌变法的急功近利和具体措施的仓促草率,感到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相。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除官职的张元济到了上海,先在南洋公学译书局任职,后又受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致力于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的编译出版和现代教科书与中国学术典籍的编辑出版,以出版的方式继续开启民智,传播西方种种学术思想,从此奠定了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地位,使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出版小作坊演变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出版重镇。
本着一贯的维新思想,在南洋公学译书局任职时,张元济就率先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既是汉译西方经典著作系统进入中国的开端,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正式传入中国的重要标志。为了更好地开阔国人的视野,培育国人的国际思维,引入西方学术思想,1901年张元济在上海创办了《外交报》。正如其定名一样,《外交报》立足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国际时政问题的刊物,不少新思想、新观点得以广泛传播。严复著名的《与〈外交报〉主人书》就刊发在该刊的1902年第9、10期上,系统全面地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谬性进行了批判。其文其刊均风行一时。受邀入主商务印书馆后,他一是组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广延通晓外文的翻译人才,搭建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平台,开始系统地出版西方学术著作;二是革新教科书的出版,在教科书的编写中另辟蹊径,以西学新知浸润社会,实现其“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宗旨,为新学提供教学支撑,体现其讲求种种学术,开启民智的一贯思想。其间,不仅出版了严复、蔡元培、林纾等人翻译的西方各类著作,也出版了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等国人撰写的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回眸历史,伴随西学的东渐,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仍是商务印书馆历经百年的不倒品牌。
可见,真正的西学东渐源于晚清时期的有识之士的大力译介传播,兴学著述,而非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单向传播所为。同时,早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大量的经史典籍就被西方传教士以各种途径带回西方各国,各国纷纷出重资译为本国文字,为此设立专门的汉文馆,组织专门的汉语翻译人员进行翻译。种类之多,内容之详,既远远超过传教士们传入中国的西方著作,更是超出人们的想象。面对西方各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广泛深入的翻译研究,梁启超在《论译书》中疾言:中国人欲知本国虚实、旧事新政,反倒要从外文书籍中翻译过来,才能得知一二。如日本人写的《清国百年史》《支那通览》《清国工商业指掌》中,就有许多内容是以前中国人自己不知道的。类似情形,英文等西语图书中也有不少。他认为,造成这种“中国人不知中国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理学(谓格致等新理)史等名”。
马建忠、严复、张元济等有识之士正是鉴于西方各国对中国典籍全面翻译的重要性,而洋务领袖秉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弊端,才力主效仿西方各国的作法,设立专门的翻译书院,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全面系统地翻译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典籍,兴办融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新式学堂,兴学著述,开启民智,改进社会,使得西方思想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想来源,最终使西学东渐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一段重要印记。至于中国大量的经史典籍翻译到西方各国,却没有像西方典籍翻译到中国后一样成为西方改进社会借用的利器,成为影响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想,形成与西学东渐匹配的东学西进,正是我们在耿耿慨叹之余,需要认真思考的.
“西学东渐”历史探源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译网』 » “西学东渐”历史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