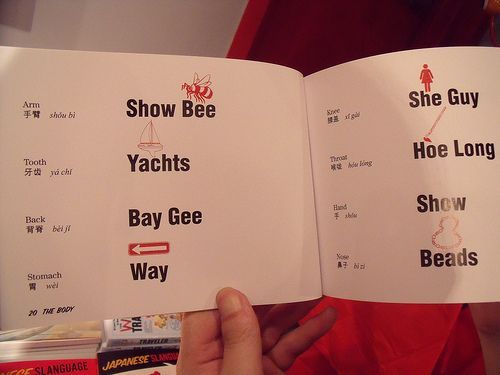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后,对翻译的需求陡增,何止几倍、几十倍!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读者来者不拒。不仅是合格的译者,合格的编辑也供不应求。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译著未免泥沙俱下。
中国应该算是翻译大国。自晚清以来懂得“放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开始译介域外著作,历经百年,而热潮不减。尤以上世纪80年代最近一次开放以来,国人对外来文化如饥似渴,翻译事业盛况空前,呈汹涌澎湃之势,从数量上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翻译著作不但成为各大出版社的重要部类,而且出现了若干专门从事外版书译介的出版社。翻译作为一门学问得到承认,翻译而成为“家”,有自己的学术团体,这种情况似乎世界上只存在于日本和我国等少数国家。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法之后,我曾以为由于需要增加购买版权的成本,可能会影响我国外国著作的出版。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完全是多虑,各出版社竞相购买外版书的版权,方兴未艾。从市场规律看,当然是因为有读者。这首先是好现象,说明国人开放的胸怀,摆脱了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宿疾。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思想文化领域,我国有震撼力的原创性的作品较少,对本国和外国读者还缺乏吸引力。不论对这一现象如何分析,我国是翻译大国,则是不争的事实。
翻译之为业,业内与业外理解有很大差距。在一般人,特别是不懂外文的人看来,只要懂外文(不论程度如何)的中国人,拿着字典就能对付。惟内行知其艰苦,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作者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往往更愿意自己从事研究著述,而不翻译他人的著作,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毕竟是为人作嫁。前辈大师如严复、鲁迅、巴金等从事翻译是抱着“偷天火”的精神,以此为“治愚”(严复语)的启蒙工作。他们创作和翻译两不误,都可以传世。还有一种情况是翻译本身就是专业研究,如傅雷译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其译文也成为经典。继承这一传统,随后的一批外国文学专业研究者,其翻译著作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并蔚然成家,尤以法国文学令人瞩目。此类文学翻译之成就可以使我国不懂外文的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专业,以至于相当一段时期许多大学的这个专业设在中文系下。尽管我本人对此一直持保留意见,但外国文学译著之规模可见一斑。然而,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很特殊的颇具讽刺意义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繁荣与翻译著作的总体质量,居然形成了反比。这是我国1949年以来特有的现象。个中道理且听我道来:
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初衷在于“文学”,志在以语言为钥匙,撷取域外文化的宝藏。但是到解放以后临毕业时听报告,说是外语人才属于国家急需(此时“文”已变成“语”),因为解放区来的干部多不懂外语,需要大批翻译云。所以自那时起,外语作为一种工具,懂外文的人除少数老革命外,多被列为政治上不强,但有一技之长的可用之人。服务对象是不懂外文的政治干部。我和全国许多学外语的学生毕业后都被分配在涉外单位,主要做口译工作,即使做文字翻译,也是声明文电类的,在严谨方面要求很高,但难有文采可言。当然仍有少数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不过在那种环境下,研究受到很多限制,还是以译介为主,而且可以想见,西方文学只限于少数“进步文学”,书店中多见的还是苏联文学作品和在苏联仍被肯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当然,外文界人士比我有发言权,我不敢妄评,只是在自己的印象中,那时不论是西方的还是苏俄的翻译著作,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可谓少而精。因为那些译者都具有专业水平,他们少了自己研究、创作的空间,遂把精力投入翻译事业,大多认真、敬业。这种情况堪与乾嘉时期训诂学发达相比拟。
到“文革”时期,百业停顿,更谈不到翻译出版外国书籍。但是享有信息特权的极少数人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还是对此有所需求。特别是“乒乓外交”之后,更有实际需要。除新华社一贯承担的参考资料从未间断外,还需要进一步对外界作更广泛深入的了解。那时“有一技之长”的外文人才已经都下放干校,正在“战天斗地”中接受改造,乃至“批斗”,有关方面想起这些人还可一用,就组织他们翻译一些经过挑选的西方或“苏修”作品。其中不乏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费孝通、冰心,都参与了《世界史纲》的翻译。于是出现了一批供“内部参考”的翻译书籍。译者是决不署名的,大多署“××五七干校翻译组(或‘学员’)”,也有同义反复干脆就以书名命名翻译组。这些真正的无名英雄以其一流的学养和已经成为本能的严谨学风外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生产”出一批名副其实的“精品”,为当代翻译作品之最上乘。虽说是内部只供一定级别的干部阅读,但是随着“一定级别”的干部陆续解放,这个圈子迅速扩大,外加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同学、朋友的朋友,争相传阅,读者的数量也就可观了。记得传到我手里的几本书,中文之老练、漂亮,知识之到位(就是不出现望文生义的外行话)令我惊讶,至今记忆犹新。总之,在知识分子普遍遭厄运,被作为“废物利用”而奉命执笔的形势下却因缘际会使翻译著作的质量达到极高的水平。这种类似黑色幽默的情景也是我国特有的,外人和后人都难体会。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大变,情况众所周知,不必赘言。一方面,许多高水平的有潜能的译者有了独立写作的机会,自然选择自己创作而不愿做翻译;另一方面,对翻译的需求陡增,何止几倍、几十倍!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读者自然不那么挑剔,来者不拒。不仅是合格的译者,合格的编辑也供不应求。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译著未免泥沙俱下。记得有一次一位青年朋友对我摇头叹息称,她认识的同学中只读过初中的,下放回城后突击补了一段外文,竟敢承接马克斯*韦伯著作的翻译(那时韦伯在我国开始走红)。这就是上面所说只要懂点外文,拿着字典就可以进行操作。这种状况延续至今,可能初中生已换成博士生,但翻译粗制滥造的现象并不稍减。因为需求更大而出版更商业化。许多国外畅销书需要赶时间,更加无暇“洗泥”,甚至出版方就明确向译者提出“宜粗不宜细”。有一位比较认真的译者亲口对我说,她承接了一部当时在国际上走红而学术性很强、注释很多的著作,几个人分头译,名义上由她统稿,但出版社给的时间极短,根本不可能细读,难免错误百出。出版方却只要赶上某个定货会就有销路,表示有错无妨,读者大多不懂外文,云云。这种态度可惜并不是个别人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开放与学术繁荣同翻译总体质量成反比的悖论。提出这个问题,谨就教于方家。
转自:传神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