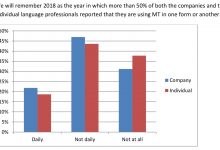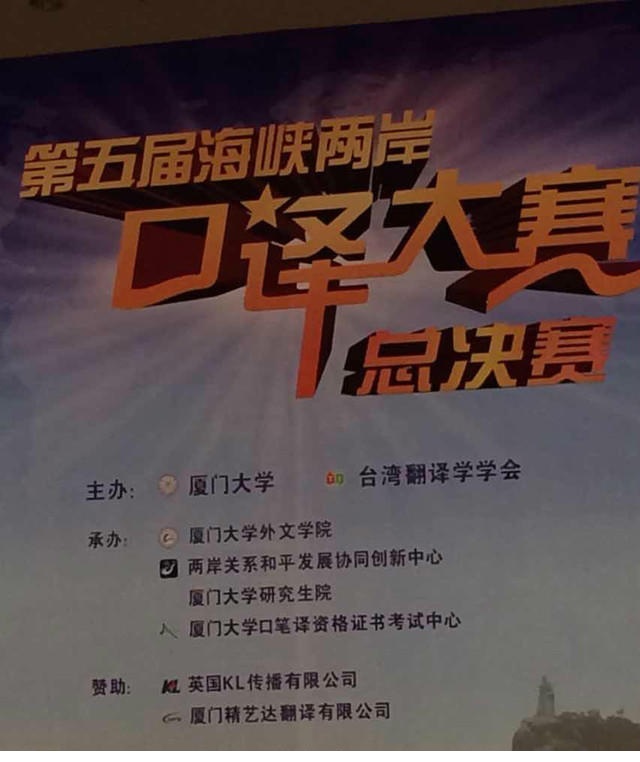翻译是牵涉到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思想、艺术交流的,含有众多因素而且错综复杂的一门学问。近一个世纪来,我国译学界尽管派别林立,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讲,弹的是一个基调―“信达雅”,各方弹奏的多半是这一基调的变奏曲。而这段时间里,国外语言学迅速发展,一些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翻译理论的研究。他们把翻译中所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进入语言学时期。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国外已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翻译语言学理论。这一理论连同其它学派理论的引进,打破了我国理论界的僵局。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试图将翻译提到科学的高度加以描述,可以说比传统的翻译理论前进了一步。然而,这一理论,尤其是其中的等值概念的引进,对我们的译学研究究竟有多大借鉴价值?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为了把翻译提到语言学高度加以阐述,于是就运用语言学中现有的,规范的术语和概念来解释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各种语言学派满腔热情的翻译理论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把翻译等值(translation equivalence)作为一个中心概念,然后围绕这个中心对其它问题进行探讨。这样就把翻译理论的焦点从传统的“直译”与“意译”的分歧转移开来。多年来,equivalence(或equivalent)一词一直被认为是翻译定义中的基本概念。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首先看看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几个代表人物为翻译所下的定义。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的翻译定义是:“翻译可以作如下定义:一种语言(原语)的篇章材料被与其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目的语)的篇章材料所替换”。〔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follows: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SL)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他甚至坚持说:“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找到对应的目的语的问题。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给翻译等值的实质和条件做出定义。”
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给翻译所下的种种定义可以说是翻译等值这个中心主题的各种变体。美国语言学家兼翻译家奈达根据自己翻译《圣经》的切身经验认识到:绝对的翻译等值是不可能的,卡特福德的定义有些过于武断。于是将翻译的定义修改为:“翻译是指接受语复制原语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等值,首先在意义方面,其次在文体方面”。(Translating consists in 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尽管他们分别以不同的语言学模式为基础(卡特福德以韩礼德的系统语法的理论模式为其翻译理论的基础,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为基础),经过比较不难看出,这些定义极为相似:每个定义都是围绕着中心词equivalent展开的,虽然奈达的定义更明确一些,但equivalent一词本身却仍然没有详细说明。
什么叫做等值?是单词、单词的音段或者更大一些的单位,人们对这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一开始就提出了疑问。后来渐渐地出现了“翻译单位”(translation units)这个概念。翻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以对比语言的结构特点为出发点,将不同语言中的话语肢解为不同层次,翻译单位被理解为介于词层或句子层之间的切分成分。对于任意一个句子及其译文,当无法以词层对比时,就指为词组层翻译;再无法对比时,就指为句子层翻译。按照提出翻译单位的理论家的说法,在这些翻译单位或整个篇章层之间即可求得等值。如何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这一点即便是提出这一理论的人也感到头痛。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一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价值。所谓偏低层次或偏高层次的翻译不过就是翻译方法中直译与意译加上语言学术语后的翻版而已。将语言现象肢解成不同层次的对应物进行对比毕竟不是翻译学研究的主要间题,也难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又把篇章视作是翻译单位的线性排列,他们认为翻译是一个根据上下文逐次从目的语中选择出与原语对等的范畴和项目(items)的过程,原语中的范畴和项目在目的语中都有一套概率不同的、可能的等值。在这种方法中,翻译包括确定翻译单位,从目的语提供的二套可能的等值中选择出所谓理想的等值来。翻译也就是一个涉及一系列翻译单位替换问题的过程。
这种论述似乎很有道理,但其根基很不牢固:它预先假定了不同语言之间的一个对称度,这就使得假定的等值成为可能。这种理论仅仅是对翻译中的语言形式进行客观的观察、对比,它并非是对翻译的真正过程进行描述。相反,它是把描述翻译过程和罗列语言转换规则等同起来,这一出发点就大谬不然。首先,我们知道,就语言而论,翻译是无定规的,翻译时往往要发挥译者的创造能力。翻译工作者为提高译文的质量而付出的努力应是永无止境的。再者,由于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或表达方法的种种差异,两种语言很少表现为一一对应关系。在两种语言的表达中即令有些巧合的现象,也只是因为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在思维方面近似或契合。如:heartbreaking―令人心碎,walls have ears―隔墙有耳,等等。但更多的是由于思维差异引起语言上的差异。正是因为两种语言的差异,原文的可译性总是相对的,绝对的可译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汉外翻译中至今仍遗留着一些不可译现象。根据以上分析,对翻译中能否采用等值这个概念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让我们首先考证一下equivalence和equivalent两词的来历。
150多年来,英语中的equivalence一词一直被用作一个专业术语,在不同的精密科学里指代若干科学现象或过程。在数学和形式逻辑领域里,它表示一种绝对的对称和平等关系。与此同时,equivalence在一般英语词汇里又被用作模糊词语。据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考证,形容词equivalent最早出现在1460年,而名词equivalence在1541年才有所记载。换句话说,equivalent/equivalence二词既被用作具有严格定义的科学术语,同时又可用作具有模糊意义的普通词汇,意为“具有相似性”,或“基本相同”。正如弗斯所指出的,英语翻译理论最初引进equivalence一词时使用的是它为普通词汇时的模糊意义。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即使在同一种语言里语言学家对equivalence一词的使用也有所不同。在语言学里,这个问题被乔姆斯基在转换语法里使用的逻辑性词语equivalence。弄混淆了。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而且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间接地产生了影响。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六十年代的著作里equivalence一词的出现多具有教条意义,而弗斯早期的使用或目前的使用多具有语用的色彩。
认识到翻译等值不能按照绝对的对称来理解,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对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思考。他们对equivalence一词进行限定和分类,这样就产生了等值类型的多样化,为了说明对这个字眼理解的差别,让我们首先对探讨翻译等值的主要方法作个粗略的介绍。
对equivalence一词展开讨论首先由雅克布森开始。他在其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方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里说:“含有差异的等值是语言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语言学关心的基本问题。”(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事实上,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这一短语就极为矛盾,它表明了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这也是翻译的中心问题。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概念是奈达提出的“形式对应”和“动态对应”(formal vs dynamic equivalence)。他从,(圣经》翻译中摘取的著名例子是“Lamb of God”。“Lamb”在英语中尤其在献祭的语境里代表“无辜”,照字面直译(即formal equivalence)可能会在另一种文化如爱斯基摩人的文化里产生理解困难。因为在爱斯基摩人的文化里,“Lamb”是人们不熟悉的一种动物,因此它毫无意义。这种情况下的动态对应应是Seal of God,在爱斯基摩人的脑海里海豹自然会和“无辜”联系在一起。奈达在给翻译下定义时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语用的求近似值的方法,因此他的翻译定义采用了“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这个短语。我们说在这一点上,奈达的确高明一些。
卡特福德的等值概念更为概括和抽象。他对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和篇章等值(textual equivalence)作了区别,并对篇章等值作如下定义:“篇章等值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与原文或部分原文等值的译文或部分译文”。(A textual equivalent is any TL test or Portion of text which is observed on a Particular occasion,by methods described below,to be the equivalent of a given SL text or Portion of text.)这个环形定义使人如坠云雾,它实际上没有说明任何间题。我们不禁要问,译文和原文或各自的部分如何才算做到了篇章等值?卡特福德描述的一种方法是:“篇章等值要靠有能力的操双语者或翻译家权威来确定。”任何从事翻译的人都很清楚,即使一些翻译名家的意见有时也大相径庭。因此,对一门科学性要求很强的学科来说,卡特福德的定义很难令人满意,对译学研究也不会有太大价值。卡特福德的方法是建立在转换生成语法所推崇的孤立的词语和孤立的甚至过于简化的句子的基础上,从这样的例子中总结出来的“翻译原则”要对付实际翻译中出现的种种复杂难题谈何容易。
随着翻译研究的广泛开展和深入,国外一些学者在八十年代又重新对等值一词进行了探讨。1981年,罗斯在一篇论述翻译复杂性的论文中明确提出,equivalence一词应由较为含糊的字眼similarity来代替。同年,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里指出:“诸如翻译单位,翻译等值,翻译恒性等之类的论题都是需要摒弃的―要么太理论化,要么随机性太强”。(Other subjects,such as the unit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 equivalence,translation invariance…I regard as dead ducks一either too theoretical or too arbitrary.)一些德国学者也认为,equivalence一词不但不够准确,经过二十多年的争论其定义仍含糊不清。另外,它还给人一种不同语言之间具有绝对对称的错觉,而这种对称除了含糊的近似值层次外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它歪曲了翻译的基本问题,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没有多大用处。
综上所述,由于每种语言都有自己所特有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背景,所以不同语言之间尤其是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往往在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正是无视这些差异的存在,而采用了一个不切实际且过于理想化的等值概念。由于出发点的错误,以等值为中心而进行的翻译研究不仅无法阐明翻译中的许多问题,而且还歪曲了翻译的基本问题。由此,笔者认为等值一词不宜用于翻译研究,对翻译实践尤其是汉外翻译也没有多大的指导价值。
引自:《中国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