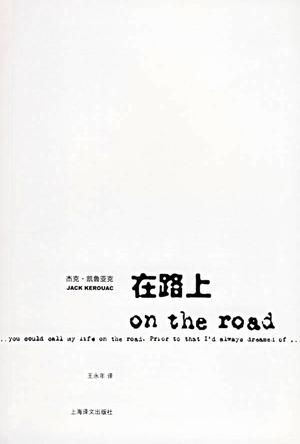近日,一本名为《捷克文学史》的学术专著,引起学界有关人士的热切关注。该书作者是捷克语翻译家、《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中文译者蒋承俊。当记者试图与作者取得联系时,发现蒋承俊已于今年5月病逝,享年74岁。据悉,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即使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她还与人合译了捷克作家雅・哈谢克的传世之作《好兵帅克》。她的离去也再次引发了一个话题:中国的东欧文学、乃至整个小语种翻译研究的断层该如何弥补?
二十多年潜心研究填补空白
“当我看到一千多张密密麻麻的稿纸时,感到很震动。居然有学者凭一人之力,经过二十多年潜心研究,完成如此厚重的文学史著作。”该书责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桂乾元告诉记者,该书是自由来稿,自己原先跟蒋承俊并不认识,出版社完全是因为看到这本书潜在的重要学术价值才决定出版该书的。“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国内首部系统介绍、评点和研究、总结捷克文学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其意义不言自明。”在编稿期间,因为稿子本身已经比较完善,桂乾元较少联系蒋承俊,不过知道蒋承俊是在得了重病的情况下写作这本书的。“这么一沓手稿,都不需要太大改动,可见她严谨治学的态度。”他还说:“每一个领域的开拓者,都是要付出很大努力的,不能不佩服蒋承俊在治学道路上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
蒋承俊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波希米亚学专业,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进行捷克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她患病后从前年8月开始化疗,因并发症于今年5月24日3时07分逝世。在老友晨光的眼中,蒋承俊在工作上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他非常感动。正是这种精神,让她在捷克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很多同龄人一样,蒋承俊在“文革”前后耗费了大量时光。为此,在一篇回忆戈宝权的文章中,她说:“留学回国后,足足被折腾了18年,现在我只有拼命地工作,把失去的光阴找回来。”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在1979年,就翻译出版了捷克著名作家、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完成《捷克文学史》之后,在和病魔作顽强斗争的同时,又和人合作,翻译了捷克20世纪文学经典《好兵帅克的遭遇》。此外,她还写了一个15万字的该书的缩写本。
晨光说,蒋承俊在病重期间,经受过难以想象的痛苦折磨,但她表现得很坚强。“她从不把她的痛苦表露出来。令人欣慰的是,她的研究和翻译捷克文学的理想和计划在她生前实现了,没有留下遗憾。”
小语种翻译研究前景堪忧
蒋承俊的离世让人们再次聚焦当下东欧文学翻译研究令人堪忧的现状。她离世前留下的新版《好兵帅克》,比起以前那些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版本,更显弥足珍贵。但是,我们还能不能继续看到这些直接翻译过来的原译本作品呢?还能看到多少本呢?令人揪心的事实是:现在我国专门从事东欧文学翻译研究的专家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七八人,他们中年纪最小的也已70岁了。
冯植生是这七八人中的一员,也是蒋承俊的好朋友。他说中国对东欧文学研究的断层早就存在,自从1996年之后,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的东欧文学室便再也没有进过新人,而林洪亮是老人中最后一个离休的。这批老人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东欧学习回来的,但是他们退下后,招不到人了。老冯说: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商品社会,学习小语种的孩子愿意去外事部门和商务部门工作。但是他也强调,东欧文学有一定地位,现在出现的情况却是,那边有人拿了诺贝尔奖,国内却没有人了解。比如,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引人瞩目的回忆录《世界美如斯》的中译版迟至去年才现身。而参与翻译该书的翻译家杨乐云,也参加了从1999年开始的翻译赫拉巴尔文集的庞大工程。只是到了今天,距离这位捷克文学大师的19卷文集中译本全部面世依然长路漫漫;而当年杨乐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东欧文学组,几年前早已解散了。
林洪亮也提到,波兰、匈牙利等国有着很丰富的文学内容,但却没有受到国人的重视。现在越来越多的东欧文学需要通过英译本再转译成中文。他做了个比喻:“本来是菜,转一遍是汤,再转一遍,连汤的味道都没有了。”对于东欧文学目前在国内的研究现状他很是感慨:“现在的研究者基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这是一种悲哀。”
事实上,不仅是东欧文学,整个“小语种”翻译研究的现状也不容乐观。据有关人士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的百分之三四十都是翻译图书。只不过翻译的渠道、数量、引进速度都比过去大大增加,翻译所担负的任务也多元化:文学翻译的主角地位,在科技、哲学、经济等图书数量惊人的译介需求之下,显得力不从心。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文学翻译,依然是星罗棋布的。除去用法语写作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捷克文学大师哈谢克的作品已得到翻译家星灿的直接译介。接下来,捷克的伊凡・克里玛、赫拉巴尔,波兰的米沃什、凯尔泰斯・伊姆雷等大师的作品陆续被介绍进中国,其中大部分是乘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而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小语种翻译研究显示出难以掩饰的疲软状态。沈志兴翻译了2006年诺奖得主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可全国上下找,似乎也就他一人能翻译土耳其文学。赫拉巴尔作品的翻译者徐伟珠表示,虽然近年来捷克文学似乎掀起了一个热潮,但是由于国内出版商业化的因素,捷克文学中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没有译介到国内。“而且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但其实也有一些新的作家的作品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随着一批兢兢业业的翻译家的相继变老、故去,小语种文学翻译研究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其前景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