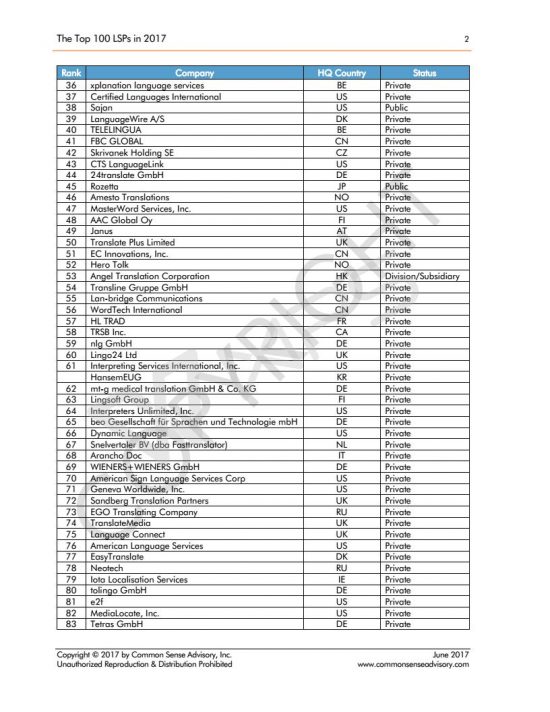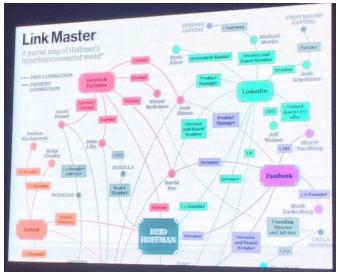【主持人语】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作家的“不客气”评价,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再度审视和探究。在全球化迫使弱势文明一再萎顿的趋势面前,信奉文化特异性的作家、评论家们辨析真相,廓清迷雾,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种评论,总归脱不掉强势文化的影子,不“君临”弱势,焉能“高屋建瓴”?然而文学艺术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正好相反,这里不承认权威。它需要的是共存、交流和互补,是个性之外的群星辉映,而不是日月对大地的单一普照。
不过,我们便因为权威的强势和有武断之嫌,就天然获得道德优越感进而自认已经拥有引以自豪的文学了吗?正如李大卫所说:“今天,中国作家仍然相信一种乌托邦式的普遍文学。他们只是在加入这场普遍文学游戏遭遇挫折时,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殊性。
看来,在“受害体验”弥漫的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还很多
――胡粲然
最近,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的谈话,再次拨动了中国文坛那根脆弱的神经。毕竟,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仅靠三言两语,就描画出一个国家文学的完整面貌。一些国内媒体在转述过程中的断章取义,则把事情弄得愈发面目全非。接受本文约稿后,我查对了顾彬访谈的全文。即便如此,我仍发现他的某些看法有武断之嫌。比如他把中国文学令人沮丧的现状,归咎于作家们对外语学习的忽视;比如他认为中国诗歌可以“活”在德语译文中―――至少我仍然相信,诗歌正是翻译中失去的那部分东西。
中国作家的任务是用中文写中国人的经验和想象,会不会外语,似乎没那么重要。学会了当然也好,但这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对于当事人的写作未必会有多大帮助;不良影响自然也谈不上。总不能说一个网球手技艺低于同侪,是因为他不擅长高尔夫球。我觉得,对外国事物的熟悉程度,更多影响的是一个人写作的对象和情调,而不是基本品质。缪斯只看中膜拜者的两样品质―――诚恳和天赋。如果说中国的文学从业人员应该学习外语,那首先也是编辑和评论家,而不是作家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言必称德里达、詹姆逊的新潮人士。现在一提外语,约定俗成指的就是西方现代的强势语种,我觉得如果有谁能说阿富汗语、克罗地亚语或是斯瓦希里语,倒是显得蛮酷的。外语这东西毕竟太难,要学就得花功夫;半瓶子醋的语言知识,往往是洋奴的随身行头。文人饭局上的那些“散装”外国话,难道还没让我们受够吗?
我不懂德文,对顾彬的翻译成就不敢妄论,也不敢想象那些中国诗歌“转世”到德语世界后的新生。差不多一个世纪前,不就有几首唐代短诗“移民”到马勒的《大地之歌》的德语歌词里,其中的一两首,至今追查不出汉语本尊?当然那些诗是通过《玉经》转译的,算不到任何汉学家的账上。
顾彬教授的最大疏失,或许是统计方面的。他声称德国汉学界翻译了中国全部有价值的作品,这种说法不仅武断而且傲慢。仅举王小波为例,他的作品便至今没能进入德国的图书市场。至于国内最富活力的青年自发写作(通常发布于互联网),就更难进入德国汉学界的视野。
由于语言差异,国际间的文学传播往往通过翻译进行。西方人有漫长的翻译历史。根据我有限的了解,远在罗马共和国末期,雄辩家西塞罗便有关于翻译的论述,虽然当时的翻译,更多被视为修辞和文法训练的一部分。11世纪十字军攻克托莱多,大量古希腊文献开始经由阿拉伯文转译成拉丁文,而苏菲派神秘主义诗歌也从西班牙传入欧洲。这一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影响,导致了游吟诗人对骑士之爱的歌咏,而后者又直接导致了后来但丁的理论和诗歌写作。当欧洲各主要方言发展为成熟的民族书面语言后,翻译更成为交流的必须。
任何翻译都会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所以我把翻译分为两种。一是从高端到低端,一是从低端到高端。前者为仿效强势语言作家提供范本,而后者更像人类学式的知识采集。不幸的是,我们的现代汉语不是国际文学市场的硬通货。抛开种种政治、经济因素不谈,这起码是一种过于年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自发产生的文学语言,所以我们拿不出普鲁斯特或是卡夫卡供外国人模仿,至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就更别提了。在最近的一次德国当代文学讨论会上,小说家徐星也提出过类似看法。所以像顾彬教授这样一个引领很多中国作家摆脱外省地位,进入国际文学共同体的权威人士,对中国文学提出一些在我们听起来不大“文学”的要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很多年里,我们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安徒生童话在中国最出名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而评价最高的美国作家,则是苏联老大哥钦点的杰克・伦敦。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王寅介绍,顾彬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领导编译过多卷本《鲁迅选集》。虽然他在鲁迅的作品中发现了“忧郁”这样一个颇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审美范畴,却又把鲁迅的伟大之处归结为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情批判,即反思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这种文化上的“吃人”现象,不但发生在传统中国,而且发生在现代中国。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说法。而且就本人对历史的粗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不是一种食人生番的文化,否则它不可能伴随一个民族绵延生存几十个世纪。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谓现代性的到来,至少没有减少发生在中国的暴力,否则20世纪的中国应该会有一段远为温和的历史。这就像德国人反省自己的历史过失,也大可不必追溯到《尼伯龙之歌》那里去(哪个民族没有几个打打杀杀、装神弄鬼的老故事?),因为法西斯主义恰好是一种极端反传统的现代化思潮。否则无法解释与其相关的政治实践,何以会在一些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发生。很多祸患实在赖不到文化的头上去。举德国今天的光头党和新纳粹为例,那些红脖子老粗能有几个人去拜罗伊特听过瓦格纳的戏?
顺便说句题外话:关于鲁迅,我所知不多,假如把他的很多随笔贴到博客上去,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和很多读者一样,他的作品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文化上的自我憎恨,以及随之而来的超越冲动。这恰好让我联想到一些经典的德国作家。谦谦君子歌德说过这样极端的话:应该把德国人遣散到世界各个角落,既是为了充分培养他们的内在美德,也是为了其他民族的福祉。将近一个半世纪后,这句话又被托马斯・曼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引用过。
当然,说出这种话的都是德国的知识精英,他们是康德的精神嫡裔,是崇尚启蒙思想的泛欧主义者,但他们似乎没有提到,酿成德国历史惨剧的民族主义狂热,恰好就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冲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惨剧在德国发生过,在伊拉克发生过,在俄国发生过,在土耳其发生过,在日本发生过,在中国也发生过。单靠忧郁是不够的。尼采也很忧郁,三岛由纪夫也很忧郁。当然,顾彬教授对法西斯主义充满了可贵的警惕。这从他对那本叫做《狼图腾》的通俗读物的评价中看得出来。我知道那是一个来自一个有过惨痛历史的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善意提醒。《狼图腾》那本书我在书店翻过。唯一的印象是,你完全可以把每个以狼为主语的句子,替换成党卫军或是红卫兵。而事实上,狼文化―――假定狼有文化―――的特征不是它的攻击性,而是其湮灭个体意志的集体主义精神。
自从梁启超写出那篇半文半白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作家们就总是纠缠于一些达尔文主义的无聊问题,好像靠他们的几本小说就能把中国引向超英赶法的现代化道路上来。中国文学就是从那时候起,变得没劲的。因为作家们热衷于把小说变成“大说”,用拗口的书面白话文,图解他们对文化、历史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的幼稚想法,以为非如此不能加入那个世界现代文学的共同体,就要被开除世界文化的“球籍”。倒是鲁迅,很早就看出那个想像中的世界不是“平”的。他翻译过一些小语种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平等观念;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文学成就和作家所属国家的国力强弱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他见识上的过人之处。
早在1827年,歌德曾经这样宣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无谓的概念,因为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而每个人都应为此而努力。”19世纪,不止一个德国人说出过这种气象恢弘的话来,比如席勒那首由贝多芬谱写成合唱的《欢乐颂歌》,以及卡尔・马克思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一百八十年后的今天,歌德的预言远未实现,至少在西方之外。当初,这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提出上述论断的根据是,翻译家们将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成为各民族观念的调停人。然而现实却是,翻译家们在这场文化地缘政治游戏中扮演的,不仅是调停人,而且是他国作家文学成就的裁判员;在翻译家的背后,还有出版商、评论家等等。他们共同决定了哪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可以被翻译、出版、评论和阅读。
文学交流不仅仅是一个彼此阅读的过程,它还涉及到交易,而文学作品的价值,而且是极大一部分价值,就是在这一交易当中实现和增长的。在这一所谓的符号经济活动中,作品―――它只是作家“码”的一些字,而字本身是不值钱的―――价值需要通过作为权威的中间人的认可来实现,否则很难从读者那里兑换出什么来;这些认可来自文学奖,或是外国文种的翻译。于是作家们就会在简历中,强调自己的作品曾被翻译成若干种外国文字,介绍到境外;而那些外国语言的排列顺序,也几无例外地写成英、法、德、瑞、意、荷、日,等等。为了加入那个叫做“世界文学”的交易场,作家们声称自己的作品在国内被禁,或是不能完整发表,因为他们反抗官方体制,或代表少数族裔,或是最后的波西米亚人,虽然这些说辞大多不堪深究,比如一本禁书如何能够畅销。总之,你得给自己设计出一个弱势然而“性感”的形象,虽说你和严格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最多只有一点血缘上的关系。
有交易就会有竞争。如同汽车、软件、手机或香水,文学的市场同样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丛林。那些竞争中的失意者,大多站在维护所谓“纯艺术”或是本土文化的立场上,指责权势者的无知、短视、流行趣味和政治倾向,不管他们是欧洲的汉学家、美国的中国研究教授还是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评委,虽说他们的小打小闹无损于任何权势。原因很简单,指责和丑闻从来都是这场文化游戏的一部分。这至少说明作家们对于体制化权力是何等地看重。他们反对的不是权力,而是同样渴望接近权力的竞争者。瑞典皇家学院一次次遗漏掉卡夫卡、普鲁斯特、格林这样的大人物,而把文学奖授予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平庸之辈,但这并不妨碍作家们对那块金牌(何况还附赠一张高额支票)愈发虎视眈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机会由此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了,只要你所属的国家至今无人交上这份好运。同时,权势者的愚蠢错误还给了作家们一个通过怨诉表现自己卓尔不群的机会;他们中的幸运者以此积攒文化资本,在市场上获利,直到获得权势者升堂入室的首肯。这时他们,包括他们的中间人,便有机会说:他们是靠作品本身说话的。也许。作品当然不是哑巴,可单凭那若干页白纸黑字的喃喃腹语,公众是什么也听不到的,更不要说不同语种的公众。
在一件事上歌德至今仍然是对的,至少在东西方之间:文学的交流,更多是在国家、族群、语言和派别之间,而不是作家个人之间进行的。不论所谓私人写作的说法如何甚嚣尘上,一个作家总是被当作一个人群、一种文化的代言人被接受和承认的。于是,帕穆克得到诺贝尔奖,其他土耳其作家就更难受到国际性关注;一个纽约或巴黎的出版商,可能从未到过北京或是伊斯坦布尔,可他却知道一本中国或土耳其小说应该包含哪些基本元素。在他内心的存储器里,已经先验地输入了一个故事,只有这个故事,才能在中国或是土耳其这样的“想象环境”下运行。
这通常是一个关于伤害与获救的成长故事。它可以是关于一个人,很多人,或一种文化,但它总要涉及到当事者与西方的相遇;这种相遇总是被叙述为一种启蒙,帮助当事人摆脱传统的困扰,尽管启蒙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困扰,但当事者总会被引领上一条理性之路。这一启蒙过程的媒介可以是性爱,也可以是科技或艺术,虽然作者在这一自我归化的过程中未必完全自觉。这当然是一种格式化的民族寓言。假如作者按照上述原则写出一个简单的言情故事,其中还有一些高深的文化讨论,再加上一些后现代叙事结构(虽然精神上已经很不“后现代”)和魔幻写实主义成分,那它就成了《我的名字是红》。
顺便说点题外话:帕穆克这部小说的精明之处,在于作者把历史背景设定在16世纪。当时奥斯曼土耳其新近攻克拜占庭,成为地中海地区的绝对强权,而依赖海上贸易的威尼斯共和国则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也正是这一时期(即艺术史上的Quattrocento[意大利语“15世纪”即文艺复兴时期―――编者注]),后者却在艺术上开始取得辉煌成就。当时麦哈迈德二世,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希望自己拥有一幅“法兰克风格”的画像,便派使节向威尼斯索要画家。屈服于对方压力,威尼斯总督把大师贝利尼遣送到伊斯坦布尔,作为外交上的和解姿态。这一事件历史上有案可稽,那幅苏丹肖像去年还在欧洲展出过。至于贝利尼的到来是否给土耳其细密画师带来那种致命的影响,我这样的外行不敢妄断,但从郎世宁在中国宫廷的际遇推想,这种可能性或许被小说家夸大了。帕穆克的故事似乎在向读者暗示,西方文明即使没有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也能依靠其纯粹的美学力量对其他文化施加影响。
很多作家可以在国外备获荣宠,却在本土遭受冷遇(帕穆克当然是个例外)。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克纳和亨利・米勒在法国比在美国受到更多的善待。红遍各国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作者甚至为奥迪汽车代言),也是一个例子。虽然我不了解这本书是否曾在伊朗国内出版过。
上世纪80年代,新西兰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女诗人的小说《骨人》。这本书的稿子曾经被很多家大书局退稿,然而面世之后,它居然卖掉好几千册,由于机缘巧合,还意外获得当年度的“飞马”文学奖。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毛利族男孩的成长故事,他在非正常家庭中受到心理伤害,又在生活中获得拯救。这部小说我在图书馆草草翻过,就个人口味来说,读起来实在痛苦。“飞马”奖由美孚石油提供资助,设立的目的是促进国际社会对于所谓边缘文学的重视。这是当代一些跨国企业扩展区域市场的一种攻关措施,而他们推广的边缘文化,通常是某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文化。今天的全球化运动,似乎更喜欢扮演漫游骑士的角色:他责无旁贷地要把诸多“次要文化”或是“民间文化”的弱女子,从民族国家的父权夫权奴役中拯救出来。比如《骨人》就被看作一部“毛利”小说,而不是新西兰小说,尽管它的作者只有很少的毛利族血统。
于是便有了抗议的声浪。很多人抱怨说那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毛利小说。可什么又是真正的毛利小说呢?除极少数人类学专家,外国人对毛利族的知识,也就是旅游片里的图腾和仪式舞蹈。正是这些争议,把这本书进一步推上国际文化舞台。出版后的次年,《骨人》又在英国被授予影响巨大的“布克奖”,并从此成为毛利文学的经典,至今没有绝版。在中国,不也有很多作家专门热衷于搜罗冷门文化符号,从少数民族的婚配制度到古代的房中术?这些偏门文化的书记官,很难被冠以“作家”这个直截了当的称号。他们就像笑话里那个世界上唯一的玩具钢琴演奏家,他是阐释约翰・凯奇的《玩具钢琴协奏曲》的权威,虽然他最初的本意,也是成为一个不加定语的“钢琴家”。
再插一句:以上种种,并非全是我的看法。这些问题,很多西方学者都曾讨论过,我只是顺便转述他们的观点。我不是学术中人,在专家面前讨论如此深奥的题目,或有班门弄斧之嫌。用德国人的说法就是――带猫头鹰去雅典。
今天,中国作家仍然相信一种乌托邦式的普遍文学。他们只是在加入这场普遍文学游戏遭遇挫折时,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殊性。于是他们又把中国文学影响力的有限,归咎于国力的未臻理想和汉学家们水平的低下。可他们忘了,当苏联还是世界老二的时候,他们又出过多少有影响的作家;与此同时,又有多少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来自弱小国家。因为一切好的文学都是关于有趣的个人,而非无趣的集体。仅在这一点上,今天中国作家的确应该向鲁迅学习,因为他明白,在最终意义上,人是平等的,一切国家及其文化也是平等的。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老是那么势利眼。(本文作者系旅美小说家)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