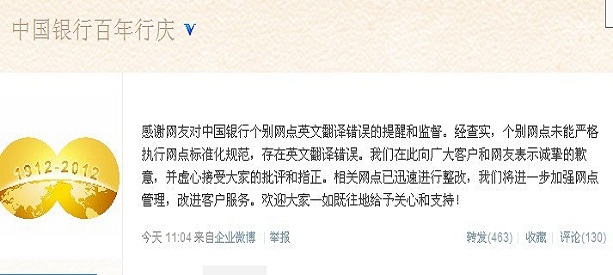草婴 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宁波,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
主要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小说12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肖洛霍夫作品(《新垦地》、《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卡塔耶夫《团的儿子》、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
■记者手记
有人叫草婴为“草先生”,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盛峻峰。他说从事翻译工作始,便用这个名字作笔名了,它缘自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与我同去探望他的吴钧陶先生问道:“你既自比作草,那这个婴字又作何解呢?”草婴先生说:就是比草还要小!
上世纪60年代始,他便是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却在上海的翻译家中拥有权威,甚至有翻译家说自己的房子是由草婴先生在人大会上代为申请的。与他初中便是同学的任溶溶先生说他有当领导的天赋,开会发言总是措辞严谨、条理分明。
采访结束,深以为然:因为这几乎是我做记者以来最轻松的采访,几乎无需提问,他已经娓娓道来一生甘苦与得失。
80年代,他把译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收获的稿费倾囊而出,只为女儿买得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如今,女儿已是著名的画家,而《安娜・卡列尼娜》的草婴译本则早就深入人心,我记得90年代初期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书店里都能看到那些封面花哨而纸薄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它们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世界文学方面的启蒙读物,而今再版的《托尔斯泰全集》装帧精美,却不知还能引起多少读者的关注?
俄国家庭妇女是俄语启蒙老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随着全家从宁波逃难来到上海,在成都南路一条老式里弄里住了下来。当时,国内首次出版了《鲁迅全集》共二十卷,定价20元,我省下父母给的零花钱去订了一套,简直如获至宝,我后来读俄文、搞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上海的租界里还能买到许多进步书刊,那时便读了许多介绍苏联的书籍,比如《萍踪寄语》、《苏联见闻录》等。
1938年3月11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国老师教俄文的小广告,就根据报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户人家。按了门铃之后,走出来一位中年俄国妇女,看到我是一个小孩子,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小孩,你来干吗?”我说我要学俄文。她说一块钱学一个钟头。父亲每个月给我5个银元,我就说我一个星期学一个钟头。
当时没有一本俄汉词典,也没有任何教材,俄国女老师只是让我到淮海路书店去买哈尔滨出版的俄语教科书《俄文津梁》。我每次去她家上课,她就根据那本教科书教我读:“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她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回家之后就反复读,读到滚瓜烂熟。
我从同学那儿得知内山书店有卖名为《露和大词典》的日俄词典,但是从我家到内山书店要经过外白渡桥,那儿有日本宪兵站岗,过往行人必须脱帽鞠躬。我找了同学梁于藩陪我去,他特别关照我说就别戴帽子了,见了日本兵把头低一低算作是鞠躬。回来时,心里很紧张,把词典夹在衣服里,日本兵见我们是孩子,也不怎么在意就放我们过去了。
日文和中文有一些相似之处,《露和大词典》能解决三分之一的问题。我对照着这本词典,跟着那位俄国中年妇女学了一年多俄语。其实,她只不过是家庭妇女,没有教学经验,连字母都没教。
进入俄国杂志,成“二战老兵”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姜椿芳先生,他早年在哈尔滨学过俄语。当他得知我这么一个中学生也在学俄语,就主动问我:“学俄语有什么困难?”我说:“困难很多,老师不懂中文,课文很难理解。”姜椿芳便约我每隔三四个星期到一个地下党的家里见面,在那儿帮我解答我碰到的难题。在他的辅导之下,我的俄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41年希特勒开始带兵入侵苏联,8月20日,姜椿芳与塔斯社上海分社商量创办中文的《时代周刊》,他邀请我参加翻译有关苏德战争的通讯、特稿等等,这本杂志影响很大,国内的人都是通过它了解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的。因为翻译通讯的缘故,我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都一清二楚,有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二战老兵。到了1942年,塔斯社又创办了《苏联文艺》杂志,我就开始翻译苏联文学,第一篇译作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若从那时开始算起,我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已经有60多年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8月9日早晨8点,我刚到办公室就听同事说:“不得了了,苏联向日本宣战了,我们也麻烦了,赶紧收拾文件吧!”不到半个小时,一卡车拿着刺刀的日本宪兵就把我们设立在淮海公寓的办公地点团团包围住了,苏联领导被他们抓了起来,办公室里的东西也被他们封存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在楼梯上看到这一幕,赶紧往顶楼跑,在上面待了三四个小时,也不知道下面的情况,就冒充楼上的居民,大模大样地走出来,日本宪兵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一出弄堂,我们就赶紧飞奔回家。好在上海的日本兵那时已经无心打仗。一个星期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翻译“娜斯佳”,打破外国小说印数纪录
1952年,华东作家协会成立,我成为最早的一批专业会员,和傅雷一起成了没有编制、没有工资、纯粹靠稿费生活的专职文学翻译家。
1955年,苏联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我很快翻译出来,在《世界文学》上连载了两期。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被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看到了,他认为这篇小说是“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并马上号召全国团员向女主角娜斯佳学习。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先是在当时发行量达到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接着又印了单行本,第一版就发行了124万册,打破了翻译小说印数的纪录。这本书成为团中央指定的必读书籍,国内很多杂志都对它进行推荐,而且在各地都举办学习娜斯佳的报告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高潮。有人说,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便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
那时,我最主要还是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从1953年开始,苏联《真理报》和《星火》杂志同时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新垦地》)第二部,《世界文学》编辑部看到后便约请我及时地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同步翻译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59年《被开垦的处女地》全部发表完毕。同样地,我还应约翻译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顿河故事》等作品。
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上海文艺界召开了一个“七七四十九天会议”,这49天里,从批判西欧19世纪文艺开始,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肖洛霍夫等进行了全盘批判,肖洛霍夫被定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而我则被批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言人”、“吹鼓手”等。
“文革”中扛水泥包,压断胸椎
十年浩劫,我两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是在1969年夏天,我在郊区接受劳动改造,突然胃大出血,连续5天5夜滴水不进,最后动手术割去了四分之三的胃,才捡回一条命。
第二次是1975年1月28日,我已经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在出版社接受批判和劳动。我被命令去工地扛水泥包,当时我的体重不到100斤,却要扛100斤的水泥包。我到卡车边等候搬运,人还没有站稳,车上人一松手,水泥包压到我身上,我只听得自己身上发出咯嗒一声,已经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我被送到工地附近的瑞金医院,诊断结果是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一公分多,不好用绷带,也没有药。加之因为我当时是“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院。医生要我一动不动地在木板上躺半年,等待腰骨自然愈合。医生对我的家人说,假如病人随便动一下,就有使断骨错位的危险,轻则下肢瘫痪,重则有生命危险。我保持一个姿势仰天躺在木板上半年,吃喝拉撒都在上面,稍微动一动就感觉天翻地覆。半年之后,我能慢慢地从木板上坐起来……慢慢地,可以下地……慢慢地,能够在房间里走几步―――这又花了半年的光景。
在这受伤的一年里,我想得很清楚,如果我不治好,那我就要变成一个废物。我想:人活着要咬紧牙关,总是能够挺过来的。1976年1月8日,我第一次走出家门。为什么我记得这个日子呢?因为我一出门,竟然就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登时如五雷轰顶。
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上海,我贴出了上海整个出版系统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叫“鲁迅痛骂落水狗张春桥”,指出他就是鲁迅当年在《三月的租界》中批判过的狄克。以后大半年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是揭批四人帮。
20年翻译完《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文革”后,我最希望做的是实现60年代的心愿:把托尔斯泰小说系统地翻译出来,我谢绝了所有行政职务的邀请,在家花了20多年的时间翻译完成12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2004年7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5年,我第一次去苏联,带了自己的一大摞译本送给苏联作协,他们很惊讶我怎么翻译了这么多作品,我说:“我也还没有年轻到可以慷慨地浪费青春年华的程度,也没有老到可以心安理得地等待死亡。”
那次友好访问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参观列宁陵墓,但我提出我想去参观托尔斯泰的故居。到了他的故居,我非常感动。托尔斯泰拥有一个占地5700亩的庄园,里面有树林与湖泊,就好像一个风景区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大地主,出身如此优越的他,却那么关心穷苦农民的生活,他想做好事,想帮助贫苦的人,但又没有成。这段心情也都记录在了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里。我认为这样一个人物是了不起的,因此他被称为“19世纪,世界的良心”。大家公认,在19世纪,没有一个作家有托尔斯泰那么大的胸襟,那么高尚的心灵。也是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影响了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尽可能多地翻译他的一些作品给中国广大的读者。
我最推崇的当然是托尔斯泰的小说,最喜欢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特别擅长心理描写,他的内心描写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个镜头,有点像电影蒙太奇是连绵不断的。一个人道主义的思想,一个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是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小说的原因。
口述:草婴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