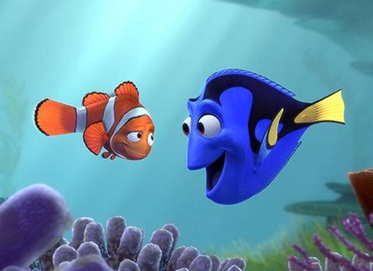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中国的文学界或者大点说文化界都要胎动一阵,我们总要猜测谁将最有资格,并且还要不厌其烦地给出一大串名字。
令人遗憾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总是毫不考虑我们遥远的热情,总是让我们言之凿凿的推测落向深深的山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让我们闪了腰: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拿走了奖金。颁奖结束后,国内文学界一片沉寂,几乎没有人为这个两个多月前才第一次以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土耳其人发言,没有人针对他拿出有分量的文章和言论。还好,我们还出了一本,还真是从土耳其原文翻译过来的。要是没有这唯一的一本,面对金光灿灿的本年度诺贝尔奖金,我们那才叫尴尬呢!虽然这样的尴尬我们以前不是没有过。
我觉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界猜不准现象”和“得奖作家的中国陌生化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出了问题。一方面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局限在英、法、德、俄、西等大语种之内,在大语种之内又非常中国式地关注大国、大作家、名作家、走红作家,而缺少一种更踏实更全面更细致更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普遍忽视小语种国家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工作,有所涉及的话也是浅尝辄止,以点带面;第三方面也是最严重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似乎与整个西方文学的大的语境、大的走向、大的趋势发生了脱节,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滞后和局限。我这么说决不是信口开河,就拿近十几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吧,至少凯尔泰斯、耶利内克包括达里奥?福、库切、萨拉马戈以及今年的帕慕克还有去年英国的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他们得奖之前,我国的翻译界对之甚少涉猎,更别说影响了。得奖之后,我们纷纷以冷门等理由予以自我解嘲,但是稍一接触,才发现个个都是大师级的,人家在获奖前,都已是极有影响的作家了。
拿今年的帕慕克来说,其1979年创作完成的处女作小说就获得了土耳其国内的文学大奖,其后的作品分别获得过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法兰西文学奖、法国文艺奖、都柏林文学奖和意大利的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同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出版,其作品《雪》在美国已卖出了20多万册,阿特伍德和厄普代克都是他的粉丝。文学评论家将其与普鲁斯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艾柯等大师级作家相提并论,并将之誉为欧洲当代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这样的作家得诺贝尔奖,怎么会是冷门呢?这样的作家获奖之前,我国对其的翻译和研究又是多少呢?用少得可怜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吧。类似帕慕克、凯尔泰斯这样的诺奖作家得奖前在我国翻译界所体现出来的空白状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确实已严重滞后于西方(外国)文学界的实际发展情况。
诺贝尔文学奖像一面镜子,至少照出了我们文学的尴尬:一方面是我们本土的作家离斯德哥尔摩距离尚远;一方面是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已经出问题了,到了需要严肃对待的时候了。
(文章来源:中国译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