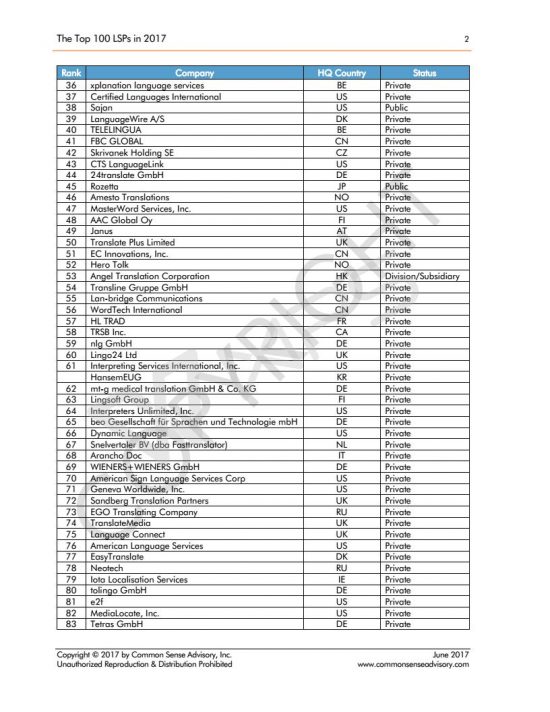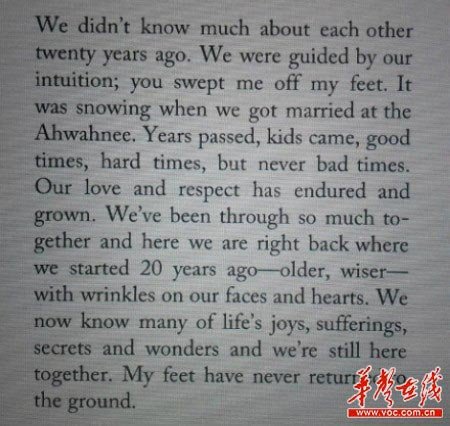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 中国翻译论坛上分别以鲁迅和瞿秋白,梁实秋和赵景深为代表发生论战,所争的题目便是”宁信而不顺”与”宁顺而不信”。林纾(1852-1924)的小说翻译反映着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宥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林译”不惜对原文进行”歪曲……这’歪’是一直’歪’到了原作的思想部分的”(茅盾),遭到了恶批,鲁迅更是称之为恶劣的政治谣言,提出了”宁信而不顺”。其后,众多译家穷经皓首,无不为之暗自伤神。信顺之争发生时, “五四”运动过去才十一二年,其时的翻译实践,翻译方法,翻译理论尚处于襁褓期,及至20世纪70年代或略早一些,另一种翻译新标准–准确,通顺,易懂–出现,也就是以明白晓畅来统一译文风格。传统翻译观对此进行批判,称其为”创作式翻译”,即中西结合式翻译。认为,忠实原则被架空,文学的特点则被有意识地”遗忘”了。真可谓一忘解千愁:”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鲁迅全集》卷七,第435页)。真正被”淘汰”的是忠实观,往往也是最具民族性的方面。忠实是顾不上了,译文由忠实原文变成服务读者。这样一来,信顺的和谐在实际操作中成了合而不偕。但是,不忠实的文本还能称作翻译吗?外文社出版的元杂剧翻译文本(杨宪益,戴乃迭译)就因’不顺’而淘汰掉了曲牌。译,似无必要;不译,即不忠于原文,有了改编之嫌。”创作式翻译”陷入身份错位,难以自证的境地。
(一)
理论上,翻译是对原本的无限接近,没有什么文本具有”不可接近性”,但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现代翻译理论证明了不可译性存在是客观的,符合辨证法的。
体验哲学和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来源于实践,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具体体验决定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在认知、概念、意义、 推理、理解等上必然存在差异。语言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所以翻译活动也是在体验和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翻译是译者基于对原文语篇各种意义理解上的,理解必定来自体验和认知。”(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因此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翻译既然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必然具有体验性、差异性和创造性。一种文化到了成熟期或稳定期是特立独行的,其特质在没被异化之前就象野生稻种一样既宝贵又脆弱,因为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任何一部作品的共同命运。作品一旦诞生,它就不再属于作者本人了, 它属于读者和观众,它的意义只能由作品本身来表述。作家所处的时代与地域的审美风尚往往直接影响着作品的语言。离开了这一语境,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就无法全面。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语言的载体-文化艺术自然会打上各个时代的烙印。中国的古典文献虽然是用我们的母语写成的,但在今天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地了解原作的文化语境,无从也无权自称是为作者的代言人。作为读者之一的译者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出现”创译”或”伪译”再所难免。
(二)
巴尔特比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那篇著名的”作者的死亡”一文中宣称,”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Barthes,1977:148);用解构主义的话来说,就是”不说出来还是某种样子,一说出来却是四不象”。 图里 (Gideon Toury)早已提出”伪翻译”说。图里所说的”伪翻译”是指名为翻译实际上根本无原文可依的译作。换句话说,就是假瓶装假酒,吆喝却照旧。在西方,”伪翻译”作品历来是用来想本土推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或文学新风的捷径,如今已然西风东渐,”洋为中用”。”伪翻译人的眼里原作只是为翻译提供了一个平台, 为在自己的文本中加入’某种特质’,或为使读者联想到’某部源语文本’提供了便利”(封一函 《再创作的伪翻译属性》)。以达到使读者”知之 “、 “好之”、”乐之”,淡化或隐去作品真实面目。伪翻译的概念也曾被拉多(Gy?rgy Radó)用来指过分偏离原文的目的语文本,以至于这种目的语文本很难被称为是翻译文本,拉多认为是否可以称作伪翻译,要视其与原作的背离程度而定。根据原文编译成的目的语剧本或称为”同构”者等都可称作伪翻译。译者的翻译观是一种建立在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基础上的归化式忠实观,持这种翻译观的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往往会剥去原作的特定形式,留下原作的内容,经过一番符合读者人文价值观标准的整合,被”翻译”出来了。这时候的译作,连典型的外在标志都没有了,译者还有什么理由对那已死的原作者说:”我是忠于您的。”
(三)
如果目的语读者翻开一部中国元杂剧关汉卿作品(下称关剧)英译译本(杨宪益,戴乃迭),他会发现,要把它们排演出来殊非易事:那些被排成诗歌体的非文非白的段落该怎样去演? 吟颂?窦娥怎么会象一个绅士或淑女一样去吟诗。歌唱?曲谱何在?他不会知道译者本来也没打算让他知道他读的作品已被动过手术了;他更不会知道关汉卿决不仅仅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们两个就象戏剧和话剧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再如果,一位母语为汉语的读者也读了这些译文, 竟然发现是读过了英语译文才”读懂”了原文,”认识”了元杂剧,更不知译者是欣然,还是惶恐。第二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容置疑:一方面当然要”归功”于目下汉语教学式微,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知识教育的不力,而英语几乎由外语上升至第二语言,以至形成了英格力士至上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因为译者对原文进行了一番拉近、整容、瘦身,将其变成了一部好懂的依托元代的现代古装戏。假如大家都看它不象元剧,真让人怀疑译者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了。关剧译文读完以后的总体感觉是:戏还在,曲已亡;人依旧,境已失。象是披上了汉装的英国戏剧,外国味十足。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会唱鹧鸪, 舞垂手,会打围,会就鞠,会围棋,会双陆”的关汉卿的作品。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称之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这位”驱梨园领袖”的创作情景是不难推测的:他手中拿的决不只是毛笔,应该还有丝竹之器。他徘徊在那些或低婉或凄凉或激昂或雄浑的捻熟曲调中,时而轻调丝弦,时而奋笔疾书。史载,他的身边一直有一位名叫李怜秀的红颜知己,既是他的模特儿,试唱者;也可以说是他的合作者。如果说思想内容是戏剧的灵魂, 曲调则赋予杂剧以容貌,使它形神兼备传唱至今。
元代杂剧,旧时或称为”元曲”或元剧,它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高峰。这个时代的大量剧作,被后人直接采用或经过不同程度的润色 、加工、 改编,七百年来一直活跃在祖国的戏曲舞台上,表现了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因而也足以说明元代杂剧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就极其历史地位,主要是看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塑造的艺术典型的生命力 艺术形式的新贡献极其对后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从这些方面看,元代杂剧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仅就艺术形式一个方面论, 就是很值得称道。元代杂剧利用唱、 白 、表演等手段,在舞台上艺术到再现一个完整的现实或历史故事,发展成为综合性艺术,既真正意义的戏剧,对中国戏剧发展史做出重大贡献。这里就涉及构成戏剧的主要因素–戏剧结构问题。戏剧结构是戏剧美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普通读者阅读和欣赏杂剧文学不了解其常识问题是做不到的。原文中被改动最大、 被译文完全被屏弃的恰恰就是曲牌词名。这些曲牌各有来历,是写给当时的演职人员看的。正是它们,告诉读者关汉卿的作品的性质。它们的意义很类似于现代乐曲的”A 调” “B调””C调”等。”端正好”、 “集贤宾”、 “斗鹌鹑”等是曲牌,即曲子的名称, 它们的曲谱大都是固定的, 散曲作家一般按照原定的曲谱填词就是了。更为复杂的还有宫调的使用,各宫调的音色不同, 很容易和人的角色联系起来。时间的流逝使我们不可能再现关先生的原曲原调, 但打开他的作品,仍让我们感到扑面而来的优美曲风。典雅别致的曲牌名有着独特的音美韵美意美。读,则朗朗上口,观,则赏心悦目,启人遐思,其美学价值不容置疑。但是在译者的观点里,这些元杂剧的显性却无足轻重,一删而就。翻译是不是可以对原作做出这样的取舍呢?有所舍之后还能称之为原剧译文吗?拉多(Gy?rgy Radó)认为,”改写或编译是否可以列入伪译之列,取决于译者是否声明,如果以改写或编译的名义出现,那么在本质上与所谓的’真翻译’并没有区别,只是在处理技术上或策略上有差异。但是,如果以翻译的名义出现就可能是再创作”。恐怕元剧译文只能是”再创作”。
结束语
我们也许大可不必对此过于关注,因为在现代人看来,关汉卿的作品已非曲本而是另一种文学形式–剧本了。这些曲牌也就似乎渐行渐远,成为古董了。假如关汉卿泉下有知,这位”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恐怕也只会象现在那些作品被电视电影改编的作家一样有口难言。让关剧的模糊面目清晰起来,宏扬中国文化,译者责无旁贷。
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语言的差异、 文化的差异 、政治的差异 、伦理的差异 、科技的差异等等,一个民族 、文化或国家,如果不再引进差异,它就会闭关自守 、固步自封 、坐井观天,如井底之蛙。文化身份错位是可怕的,文化内涵的丢失更是不可饶恕。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反对以读者的名义来欺骗读者 、背叛原作、 扭曲他人的文化身份。翻译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不言自明。有鉴于此,建议元曲的翻译文本的编者和译者对文本作些说明较为妥当。
(来源:人们网安徽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