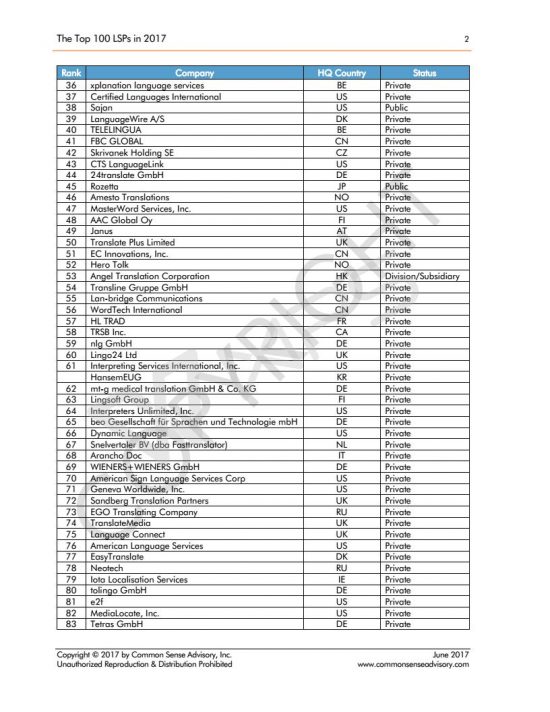提起文学翻译,首先要谈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水平如何,用什么作标准?在我国翻译界一向有个流行的说法,谓之信、达、雅。
信者,忠实;达者,达意;雅者,传神也。换言之,亦即准确、畅达、传神之意。如果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忠实于原著表达出原意,传出其神韵。而所谓神韵,乃指原作的风格、韵味,亦即作家本人的艺术个性和特色。
我本人对文学翻译一向追求的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力求使译作在情调、韵味、风格上尽可能和原著保持一致,使读者阅读译文如同译者本人阅读原著一样,达到基本相同的境界。这里不妨以拙译《童年》为例,小说一开头,高尔基描述他父亲死后躺在地板上,“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此处原文倘按字面逐字直译应为“穿着一件白色的”,至于是一件白色的什么,白褂?白裤?原文根本没有描述,仅从字面上看根本揣测不出来。于是,我在翻译此句时,参照了另外两个译本,写下我的译文。这样,就出现三种不同的译句。这里,不妨试作比较。我国北方某出版社的译文是:“穿着白衣服”,而南方某出版社则译为:“蒙着白布”。我在见到这两种译文之后,深觉得都不能准确表达原著的辞意,亦即不“信”。而我几乎不多加思索地将句子译为“穿着一领洁白长衫”。我为什么要这样译?有何依据呢?回答是,只消看一下原文句中的“白色的”一词。就自然明白了。我们知道,“白色的”,形容词,但究竟是白色的什么,是裤,抑或是褂?还有,穿的又是几件?原文本都没明说。不过,就是这个形容词的词尾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只穿了一件!因为词尾是单数。请注意,凡熟练掌握俄语者都知道,俄文中对“数”的概念是十分注重的!你在用俄文写作时,无论是运用名词或形容词,一下笔就应当亮明它的“数”,这可与中国汉语文字大不一样。那么,既然形容词是单数,即表明是穿了一件。所以,我才有把握并很自信地将原句译成“穿着一领洁白长衫”。而且这样一来就与原著保持了一致,顺理成章地读到描述中死者“两脚赤裸,脚趾揸开;手指弯曲,搭在胸前……”。
再说《我的大学》,该书第一段全文仅两句,是一个复合句型。主句:“这样,我就上喀山大学学习了”,这一主句暂不论,单说子句,原文依序逐字直译应为:“不少于这个”,中间是个比较级形容词。这个句比较难译,汉语很难用几个字表达明白。还是那个北方某出版社的译文是:“仅此而已”,这样翻译,语意不明,文意不顺,达不到“信”的标准。而南方某出版社为图省心,干脆弃之不译。殊不知这对于作者和读者是一种不尊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我在交给安徽文艺出版社的译稿中,将它翻译为:“这样,我就上喀山大学学习了,起码也得上这所大学。”我这样翻译,能否为译界所认可呢?1996年10月,我在北京大学出席高尔基逝世60周年纪念会,就便将上述两处三种译文原原本本抄录给与会的几位专家和教授过目,他们看后,一致肯定了我的译文准确可信。
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翻译水平高低,译文质量优劣,会关系到读者的心灵感受。阅读高质量的优秀的译文,那不啻是一种惬意畅怀的心灵倘徉,是一种美的享受;而看一篇拙劣的译文,那就简直如同走在乡间的烂泥巴道上!寄语译界的朋友们,既然大家都以文学翻译为能事,那么,我们就不能让读者望文生叹,或者读之味同嚼蜡。
1987年,北京召开我国首届诗歌翻译座谈会。这可是一次译界“四世同堂”的盛会,老一辈翻译家戈宝权、孙玮等都参加了。会上曾有人提出闻一多先生关于诗歌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一说,也可以移植到诗歌翻译上来,实际上,这与“划地为牢”是一个意思。此说一出,当场便有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译诗固然要忠实于原作,但首先必须是诗,必须具备诗的要素,必须有诗的韵味。译诗主要是要传神造境,要传达出原诗中的韵味、韵律,而不能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此说正与本人译诗的初衷不谋而合。
这里,请研究一首译诗,原诗作者是被西方誉为俄罗斯三大名诗人之一的丘特切夫。原诗没有题目,这里只引该诗的第一节。我按原诗顺序逐字直译如下:
冬天难怪发脾气过去了她的时刻―――春天在窗子里敲,要把她赶走从院子里拙译经过推敲,翻译如下:难怪冬要大发雷霆,原来她的日子已到尽头,春正频频敲打着门窗,急于把她从大地上赶走。诗歌翻译在更大程度上很像中国画,在这个领域大写意小写意,或者运用工笔,都是同样可取的。我们经常说,但求神似不求形似,这固无不可,然而也不一定一概排斥工笔画。
来源:安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