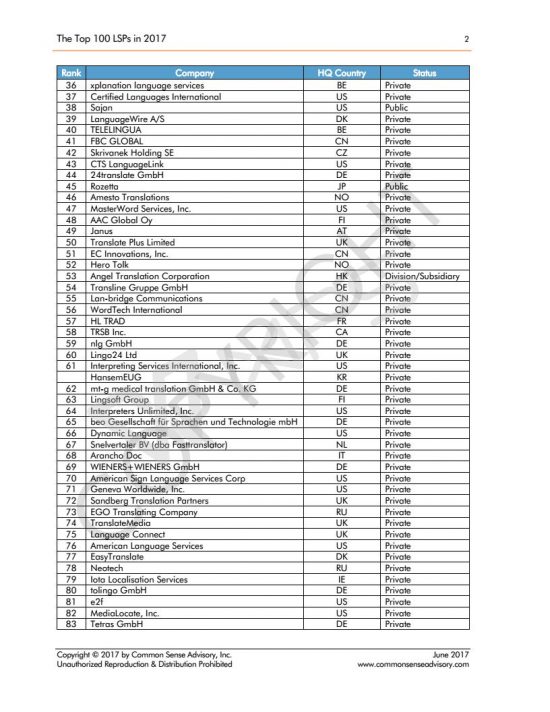克希兄的大译《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刚刚出版,便惠赠一册,使我先睹为快。仅此一卷,已有近35万字,捧着厚厚的译本,感受到的却是译者成年累月的艰辛。
翻译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语言的差异、时代的习俗和译者的风格等等。因此随着社会的变迁,每隔若干年就会有新的译本问世,家喻户晓的名著更是如此,例如众所周知的《红与黑》就有20多个译本。但是自从译林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以来,至今才见到克希兄的新译本,其中自有值得探讨的原因。
首先是原著规模的宏大。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共有七卷,译成中文约有260余万字,显然非常人所能独力胜任,当年译林出版社就是约请了许渊冲、桂裕芳、徐和瑾和许钧等13位学者教授合力完成的,这也是笔者面对大部头名著就望而却步的原因。其次是翻译的难度很大,普鲁斯特极为敏感地捕捉和把握生活中最细腻的感受,以意识流的笔法来烘托气氛和背景,其中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和行云流水般的长句,无不需要译者呕心沥血、绞尽脑汁,付出无比的精力和耐心。
克希兄当年参加过译林出版社的翻译队伍,参与翻译了其中的第五卷《女囚》,对于个中艰辛自然深有体会,而今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花甲之年独自承担翻译全书的重任,这已经不止是对名著和翻译的热爱,在我看来简直具有一种殉道者的悲壮,也就是为传播法国文学而献身的精神。
大凡有心的翻译家,往往在翻译的同时潜心研究,总结经验,例如许渊冲先生总结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三化(深化、等化、浅化)和三之(知之、好之、乐之)论,罗新璋先生总结的三非(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等。克希兄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他不仅翻译和重译了许多法国文学名著,而且出版了随笔集《译边草》,总结自己数十年来在翻译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碰到的各种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实际上为晚年从事这一宏大工程奠定了基础。
当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追忆似水年华》,译者均为资深学者和教授,风格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与13个人的合译相比,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译本显然有许多优点,至少在风格、译名等方面要更为统一。克希兄早年专攻数学,曾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数学28年,具有陈景润那种老黄牛般的勤奋精神。他本来通晓英语,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进修期间又熟练地掌握了法语,后来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担任编辑,接触了各类名著,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电影、音乐、绘画等方面都有深厚的修养,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克希兄都可以说是承担这一工程的最佳人选。
翻译本身见仁见智,我们不可能逐字逐句地比较译文的高低,不过仅就书名的翻译而言就有所不同。当年译林出版社曾组织译者进行讨论,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暂时采用了《追忆似水年华》的译名。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罗大冈先生说过他欣赏的译名是《忆华年》,大致也是这个意思。克希兄参照了英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多种译本,慎重地译为《追寻逝去的时光》。我现在不避事后诸葛亮之嫌,认为这一译名更符合作者的原意,因为中文里的“似水年华”,多少带有“逝者如斯夫”、“时光如水”、“韶华易逝”等感伤的哲理意味,而普鲁斯特的本意却是通过对时间的追寻来表现生命的永恒,其中并无感伤的成分。又如第一卷的译名,以前通常译为《在斯万家那边》,现在译为《去斯万家那边》,一字之差,大有深意,叙述的内容似乎都像意识流那样动了起来。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因出版《马丁・杜加尔研究》而结识克希兄,至今不觉已过去十多年了,我们也都成了年已花甲的老人。克希兄在此时承担这一预计历时九年的重任,等于是把自己的晚年贡献给了这套名著的翻译,放弃了退休之后应有的娱乐和休闲。我尽管自愧不如,缺乏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却也认为对于翻译家来说,60岁正是经验丰富、精力尚好的黄金时期,以克希兄的毅力、稳重、灵气和甘于淡泊的品格,我相信他必能圆满完成这一珍贵的重译,在法国文学的翻译史上留下一块传世的丰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