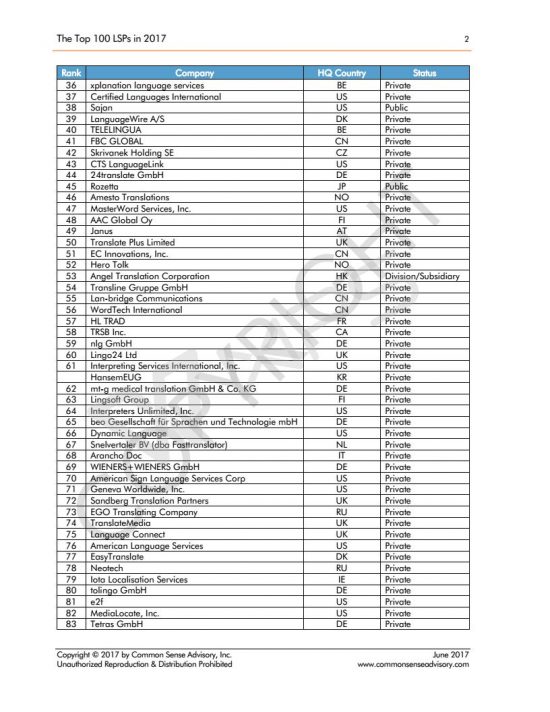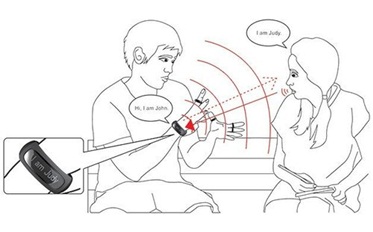从文学阅读来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法国文学这样,与我们中国读者有着如此紧密的阅读关系,以至于翻译家傅雷先生一旦去世,巴尔扎克在中国也就去世了;仿佛此前他还一直活着一样。优秀译者是如此重要,在非母语国家的阅读当中,他几乎就等于原作者的化身。尤其是当我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法国文字译本,并多次与法国读者接触以后,我更加确信了这个判断。纵观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开初都是奔着财富和领土而去,最终的胜利却体现在文化的浸润与征服上。换一个角度来说,人类付出的无数生命与鲜血,实质上都是对于文化沟壑填埋。可见不同语种之间的沟通、理解与传达,是多么复杂和微妙。具体到小说的翻译,同样也是小径纵横,危险四伏。彼时的阅读时尚、彼时的心理需求、单元性的社会因素以及原著的版本来源,等等,都会直接影响翻译小说的本意与语言质地,导致歧义的产生或者轻佻浮躁的阅读,有时候则仅仅只能制造一些名言,在大众文化领域简单地消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一句式,便是典型的一例。
19年前,我们凭借一本薄薄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首次接触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当时,我们的确脑袋一热。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刚刚结束了漫长的政治冰冻期,春天之门在缓缓开启。那时候,任何一点绿色都被视为春的使者,受到高度的瞩目和热烈的欢迎。昆德拉的小说,首先以捷克的社会背景,获得了我们的亲切认同。他直接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哲学、历史与日常生活公然糅合,其写法显得新鲜而大胆,满纸的哲学名词,让我们模模糊糊感到自己被提升到了哲学的意义上,超越了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的认识,甚至书名还可以拗口乃至不通顺,其生涩感与雅皮士感的混合杂交,引起了我们尤其是文学青年心中一种难以言状的震颤,通俗地说,就是挠到了自己抓不到的痒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欧化的句式总是比较容易得到认可和宽容,以翻译语气制造出来的名言似乎更像名言。当年,我们根本没有思考能力,去意识曾经沦为半殖民地的祖国,其洋奴文化是否还残留着余孽。当然,我们更没有想过,母语为捷克语的作家昆德拉,由于1975年移居法国而才开始尝试的法语写作,作家是否真的可以用法语表达他的作品意图?何况他的这本小说,还是由法语译为英语,再由英语译为中文的。昆德拉与中国读者之间,绕了几个语言的弯弯,中国读者是否最近距离地接近了原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更多是因为非小说因素热着昆德拉,热着他的易于解读,热着他方便我们自己顺水推舟地表现自己的哲学知识,因为昆德拉的文本充满了通俗的哲学情调。后来,我们甚至并不是阅读,而是当作句式使用。这句式逐渐流行,慢慢进入电视的八卦节目,进入网上的调侃与卖弄,成为了更年轻的大孩子们的文化品位标签,因为这个年纪的大孩子和当年的我们有着同样的毛病:需要一点哲学、一点人生真知、一点郁闷闲愁,还有一派时尚姿态:对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昨日旧恨和今日疏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式,便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从小说的意义上,昆德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我们应该凭借什么来进行选择和认可呢?
感谢许钧先生在这个时候的出现。他的法语造诣和翻译技巧的精到,使得我们有机会如此接近和了解法国的当代文学。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许钧翻译的《桤木王》。《桤木王》的文字,是那么典型地表现出了法语的细腻,繁复,感性与敏感,在久违了的巴尔扎克时代之后,我们重又感受到了法语在当代小说血脉中的经典跃动。去年,许钧直接从法文版本,重新翻译了昆德拉进入中国的第一本小说,书名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显然,这个书名在语法上是通畅的,内容的表达上也更为贴切与忠实。今年5月,许钧又翻译了昆德拉的新作《无知》。许钧的译本,终于让一个比较真实的昆德拉浮现了出来。再回首这十九年来热烘烘的混乱,我们便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冷静的结论了。显然,沉静的清醒的阅读,对于作家个人,对于中法两国颇具渊源的文学交流,对于任何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和喜爱,对于所有年轻读者的成长与见识,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比如我,现在就可以十分明确地不再喜欢昆德拉的小说。因为我不喜欢主题先行,不喜欢直白地用哲学理论来阐释主题,还不喜欢小说人物只是哲理的木偶。我更喜欢小说语言本身的瑰丽。语言是绣花线,应该五颜六色,光泽熠熠,可以绣出栩栩如生又各个不同的人物形象。法文的繁华秀丽,意绪无穷,与中文是如此相近,好比两国的烹调技艺,都是那么讲究色香味。当然,我想我不是在肯定或者否定一个作家,而是在探究如何拥有沉静的清醒的阅读。一想起我自己花了十九年时间,才闹明白一点点阅读上的问题,便感慨。写下来,也算一点自我批评吧。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