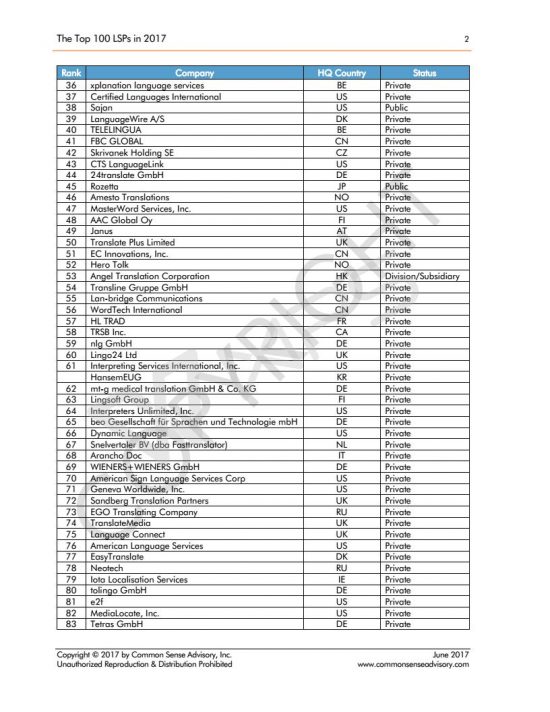随着改革开放,外国文学的春天也来临了,一进入八十年代,就开始了真正的繁荣。虽然还有春寒料峭的日子,然而这寒冷很快就被湮没在外国文学的繁花中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和出版,在中国经历了一场神话。
没有人策划,也没有人指挥,全国数十家出版社,几乎在同一时间,都突然调转目光,放下各自的传统出版物,不约而同地瞄准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和出版。出版社之众多,选题之相近,计划之庞大,出版之集中,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真是空前绝后,因而我称之为一场神话。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无疑是现代神话的国度。首先是经济,由转型而开始了腾飞的神话。与此同时,长期受压抑而又不甘寂寞的外国文学,就像年终消费而掀起购物狂潮一样,也趁机来一次世纪末的大消费,其惊心动魄的景象,只有在神话中才能看到。在回顾那种景象之前,还是先谈谈前神话时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外国文学进入新中国,必须通过一道窄门,而这道门的尺寸,是按照前苏联文艺政策的标准设计的。因此,能顺利走进窄门的外国作家,可以说屈指可数,主要是前苏联没有被斯大林枪毙的作家,以及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美作家中的巴尔扎克、斯汤达、罗曼・罗兰等,因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斯大林的赞扬,也就成为新中国的特殊客人;他们的作品,如《欧也妮・葛朗台》、《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便成为中国读者难得能品尝到的法国大餐。假如罗曼・罗兰于1935年写成的《莫斯科日记》,也像纪德的《访苏归来》那样,当时就公诸于世,而不是封存五十年,那么罗曼・罗兰早就会像纪德那样被打入另册,中国读者必然少一道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佳肴了。
不过,用《红与黑》这类西方作品来点缀那个时代的文艺,实在是双重误会。文化大革命消除了这种误会,西餐全部撤掉,外国文学在中国全面遭到禁绝。那段文化荒漠时期,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了。
随着改革开放,外国文学的春天也来临了,一进入八十年代,就开始了真正的繁荣。虽然还有春寒料峭的日子,然而这寒冷很快就被湮没在外国文学的繁花中了。
人民文学和上海译文等老社焕发了青春,有计划地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一套陆续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当时就具有权威性,不是资深翻译家的译作是进不去的。但是新的出版社应运而生,为新生代翻译家提供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天地,尤其译林社和漓江社异军突起,打破了出版业计划经济的格局,以其新生的活力,很短时间就打造成亮丽的品牌。
漓江社隆重推出由柳鸣九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后来安徽文艺社加入),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首次将这么多外国名作家集中地介绍到中国,功不可没。译林社起步则大力推介外国通俗文学,从而赢得广大读者;待到羽毛丰满,便向两个老社的传统选题打出重拳,看准人文和译文两社体制滞后和出版周期长的弱点,又利用当时资源共享、尚未确立知识产权之机,推出《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系列,每个选题总抢在两社前面出版,再加上灵活的销售策略,迅速占领市场,极大地冲击了两个老社,毫不客气地成为事实上的“龙头老大”。
打世界名著牌,短时间内就创造奇迹,我称之为译林现象。正是这一现象,开启了外国文学名著在我国的一场神话,这几乎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
回想一下那个刚过去不久的火热的年代吧!人人都想先富起来,许多民营企业家完成了原始积累(神速),许多官和商实现了双赢(神通)……同样,在出版界,译林奇迹般地成功,刺激多少出版社起而效尤,纷纷上马。当时花城社负责人罗国林就曾对我说:“你译过多少法国文学名著,全部给我。”真是史无前例的稿约。
超常,无序,无理性,几近疯狂,这是所有神话匪夷所思的特色。外国文学名著翻译出版的品种和数量,短短几年就超过了一个世纪。做出规模的出版社不下十家,其中佼佼者如浙江文艺、福建海峡、花城等,都曾风光一时。《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堂吉诃德》、《简・爱》、《少年维特的烦恼》、《娜娜》、《茶花女》等,一时间出了近十种,或者十余种译本。河北教育社尤为突出,邀请专家主编出版规模浩大的《世界文豪书系》,显示其雄厚的实力。
神话不是常态,不可能持久。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外国名著的出版就潮退浪平,那些披上神光幻色的出版社又纷纷淡出,于是进入后神话时期。
一场神话,就是一场大变革。人文和译文重振雄风,译林难称老大,即使三足鼎立也不复可望,至少河北教育已成磐石之固,北京燕山社也突显崛起了。前有译林现象,后有北京燕山现象,都为时势所造,而时势者,非人力所能易也。神话期间涌现的名著译品良莠不齐,大部分随着出版社的淡出而自消自灭了,剩下来的名译家精品则另觅下家。北京燕山适时抓住机会,请进力冈、罗新璋、宋兆霖、杨武能、陈中梅等名译家数十位,完成了《世界文学文库》的整体调整,成为这场神话的最大受益者。
有规模成系统地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中国之大,有此五家并不算多。 (李玉民)
《北京日报》